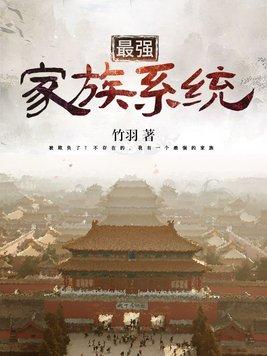秃鹫小说>剑在笼中吟 荧惑高 > 第11章 受绞(第4页)
第11章 受绞(第4页)
死!死!死!死!
明明没被酷刑打垮,却在游街时彻底崩溃。
卫筝爆发出她自己也感讶异的力量,将枷板挣得咔咔作响,可惜这斗志来得实在太迟,若有针盒傍身,若武功没有被废,想必她此时定可令那些恶人惊慌失措四散逃命罢——但她没有,一切都不过是小女囚临刑前的绝望幻想,枷板莫说作响,就是一根发丝的距离也未动。
“女犯——带到!”
绞刑台,耸立在土地庙前广场的食人妖物,卫筝被从笼车中“拆”出来时甚至不敢看它一眼。
喧天的锣鼓声盖过了典史的呼喝,她突然感觉自己变得好小好小,渺小到要从肉体中飞出去,飞到又高又远的青天,天外之天……
“犯妇卫筝!犯妇卫筝!”
地面拉近了,典史的掌掴依旧强而有力,只一下便将她打回现实——卫筝几乎不确定自己有没有答出那声“在”,她只是机械地张张嘴,然后听见典史没好气地下令:
“既已验明正身,现在便给你开枷杻,插犯由牌——规矩你懂,切莫自误!”
让我去死便是,耳鸣欲裂的小医师强撑着最后一丝精气神,呼,吸,呼,吸。
若现在针盒在手,她也不再会考虑逃脱,而是选择直接将耳膜戳破,为什么我不能直接去死呢?
子规磨打开了,但枷杻就是她的骨头,缺少那些木头她便干脆跪倒在地,肌肉条件反射般要摆出五心朝天的羞耻姿态,但最多只将臀撅高些,手心是怎样也无力翻朝上了。
幸而典史似乎有更重要的事要操心,这才没让卫筝在大庭广众下吃鞭出丑。
“娘了个腚的,刑房书吏何在!主簿,主簿呢?还有骆县丞——莫非要我和几个佐官主持行刑么!”
烦躁地扯着胡子,听着脚下这贱婊子还在呻吟,典史更是气不打一出来,索性将厚底官靴踏在那消瘦的美背上用力压下:“腰背抻直!你这犯妇还不老实,妄想袭击我等么!”
不去听被他当做出气筒的无辜女囚呜咽声,典史拔腿就往监斩台跑去,直至见到县官大老爷才略微心安。
形似长令牌的犯由牌已摆在一旁桌案上,这东西本应由刑房书吏向县官“请朱批”后送至犯人面前。
可今天不知撞了什么邪祟,书吏、主簿、县丞,这些本应扮演关键角色的家伙毫无征兆地玩起了失踪——而念及元老爷昨日交代他那句“今日恐不会太平”,典史便感到一种不知根底的心慌。
“禀县爷,那三人还未寻到,是否——”
“继续行刑便是!”
为辟邪,监斩的县官元迩在青色官袍外又套了件肥大红袍,而典史不知道的是,他眼中的主心骨县爷亦只强装镇定,藏在袍下的左手更是几乎要在袖珍连弩握柄上按出指印来。
第二批派去监视的兄弟没有音讯,定也是凶多吉少了…四处城门都无回报,公廨那边也扑了个空,这驴日的樊笼司使究竟躲在哪里?
已一日多……既跟我撕破脸皮,又为何到现在还在等待时机?
少劳兄啊少劳兄,莫非你觉得凭自己一人一剑,杀我几个下属官吏,便能拖慢行刑,乱我阵脚,或是这小婊子从我的强弩队面前劫走?
勉强压下纷乱心绪,元迩右手提起朱笔,在典史倒呈上的犯由牌上一拖,在“当绞女犯卫筝”表面留下一道红痕。
而不等典史跑下监斩台,他又阴恻恻地吩咐:“若听得劫法场示警锣响,也莫来护我,先杀那卫家婊子!”
“可县爷——”
“哪来恁多‘可’,你听命便是!”
几乎是咆哮着下达命令,元迩惊觉自己竟控制不住自己失态。坐回太师椅时,汗湿的软甲顶着外层官服,令他更感无端烦闷。
莫非还有什么我没算到的错漏?
我有两百人,六十挺连珠劲弩,凭少许手段,就是那姓安的小子横死当场也能做成铁案——钦犯暴走,上差暴死,呵,听着多么顺耳!
卫筝浑然不知那台上的杀身仇人已紧张到了何等程度,她只感觉自己膝盖已在地上生了根,能跪着是何等幸福,若非有佐官将她扯起,她几乎便要失去意识。
“犯妇听仔细了,现要给你插牌挂绞索,可还有什么遗言,速速交代!”
“我死后…必为…”
直到最后,本性正直善良的少女仍是下意识没将那些恶毒咒诅说出口来。
于是一个土瓷大碗被递到她眼前,这次不消吩咐,少女已贪婪的滚着喉咙,将那些混浊又带着酒糟异香的液体一饮而尽。
怎会更渴了…这不是水……我只是想喝口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