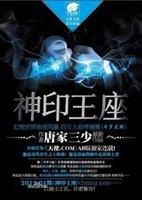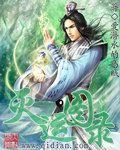秃鹫小说>祥瑞 王莽和他的时代 > 第36章(第2页)
第36章(第2页)
因此,王莽恨不能把汉哀帝从汉帝的世系里抹去,箕子和汉哀帝是兄弟辈,但王莽指认箕子继承的仍然是汉成帝的皇位而不是汉哀帝,所以,箕子是“汉成帝之后”,箕子的“外家”是汉成帝的母族和妻族——当然此时汉成帝已经没有妻族存在了——剩下的母族就是王氏家族。
卫太后和两位兄弟卫宝、卫玄在中山国巴巴等着进长安时,等来的却是另一个人:刘成都。
刘成都是汉宣帝的曾孙,和箕子已经很远了。他千里迢迢来到中山国只为一件事,当国王。原来,基于“为人后”的考虑,箕子一走,又没有兄弟,等于说中山国要“绝嗣”,箕子的父亲中山孝王也就没了香火,王莽“体贴”地考虑到这一点,让刘成都过继给中山孝王当儿子,继承中山王位,奉箕子的生母卫氏为中山王太后。同时还给卫宝、卫玄赐爵关内侯,把箕子的三个妹妹分别封君,食邑两千户,这些丰厚的赏赐有一个条件:卫氏家族要安心留在中山国当“国戚”,不要幻想到长安去当“皇亲”。
如此一番操作,从礼仪上看对卫氏家族竟然“两全其美”,物质方面也比较丰厚,但唯独把真正基于血缘的人伦之情、母子之情剔除了。
消息颁布后,大臣们都没有什么意见。偏偏冒出来一个年轻人叫申屠刚,他身份低微,仅是右扶风的功曹,相当于今天首都一个区政府的中层官员。按理说他没有什么资格给皇帝进谏,因为恰好赶上日食,王莽以皇帝的名义下诏允许上书,申屠刚这才有机会写了一封对策,要求让卫氏家族来长安,不仅人要来,还要有官做,特别是未央宫的保卫应该让卫氏家族来承担,要提防朝廷里的“霍光”也就是王莽。其中有一句话尤其显眼:
且汉家之制,虽任英贤,犹援姻戚。亲疏相错,杜塞间隙,诚所以安宗庙,重社稷也。3
申屠刚点出汉代宫廷制度的一个传统:外戚和官僚要“亲疏相错”,彼此制衡。显然,他是把卫氏家族看作“亲”,而把王莽看作“疏”。
这封对策让王莽大为恼火,要不是因为这是应诏对策,言者无罪,王莽估计会杀掉申屠刚。这次只是斥责他“违背大义”,免职打发回家了。王莽当然忌讳这篇对策,但说申屠刚“违背大义”也是讲得通的,这个大义就是“为人后”之义,王氏家族是箕子“父亲”汉成帝的母族,是货真价实的“外家”,当然是“亲”,怎么能说是“疏”呢!
申屠刚的下一次出场,已经是刘秀的大臣。为了阻止刘秀出游玩乐,他用头去顶刘秀马车的轮子,刘秀吓得打道回府。
这位申屠刚倒是一以贯之。
2.再摘令瓜稀
没人为卫氏说话,中山国的后宫一片哀号。
陌生人刘成都的到来,令卫太后母子团聚的愿望落空,她整日以泪洗面,身边的随从、卫氏的亲眷,无不感到难过。
特别是卫宝,他和王莽的长子王宇关系不错,两人常常有书信来往。他本来很感激王莽为冯太后平反,但委实想不通为什么把卫氏家族防得如此严密。正在此时,王宇秘密派人送来一封书信。
身为安汉公长子,王宇身边聚集了一批人。有些自然是趋炎附势之徒,但也不乏一时才俊。其中,有两人最得王宇信任:其一是师傅吴章,当时的儒学名家,太学博士,治《尚书》,弟子千余人,对王宇影响非常大;另一个是妻子吕焉的哥哥吕宽,尤为王宇所信赖。
王宇很想帮助卫氏家族,他并不赞同父亲,又不敢当面说,就把吴章和吕宽找来商量,已经怀有身孕的吕焉也坐在一旁。看着吕焉日渐隆起的腹部,王宇颇能理解卫太后思念儿子的深情。几个人坐而论道,认为王莽的根本依据是“为人后”之义,所以比较保险的办法,就是让卫太后修书谢恩,主动向王莽剖白对“为人后”这一儒家伦理的深刻理解和无比认同,在思想上坚定地和王莽站在一起,以感化王莽。
王宇给卫宝的密信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卫太后欣然同意,立刻上书谢恩,信中既批评了丁、傅两家的大逆不道,也引经据典地恭维了王莽。王莽看到上书之后确实十分高兴,但他认为卫太后如此深明大义,那就更不必回到长安,让箕子专心为汉成帝之“后”就够了。为示表彰,王莽给卫太后增加了封邑七千户,赐黄金百斤,中山国的官员也涨了俸禄。
这个结果令卫家和王宇都很意外。卫太后再上书谢恩,王莽就不理会了。卫太后在家难受地哭。王宇只好再找吴章和吕宽来商量。这一次,吴章想了一个新的办法,他认为王莽有一个显著的特点:
(吴)章以为莽不可谏,而好鬼神,可为变怪以惊异之。4
这句话非常重要。吴章是王宇的师傅,对王莽应当比较了解。他的这句话,应能代表近臣对王莽较为普遍的看法。“不可谏”,说明王莽极端固执,一意孤行,难以沟通,王宇之所以不敢直接劝诫父亲,想必是“知父莫如子”,说了也没用;“好鬼神”,说明王莽极其相信灾异和祥瑞,而且是真信。
所以,吴章的法子就是,让吕宽弄些动物的鲜血,趁夜泼洒到王莽家的大门上。第二天王莽发现,一定会十分惊惧,视为灾异,循例向博士们问询其中的含义。届时,吴章会站出来,将其解释为王莽不让卫氏家族来长安,所以上天才会降下这种异象。
听上去倒是天衣无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