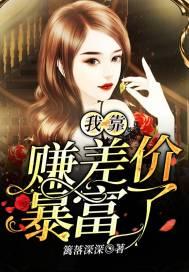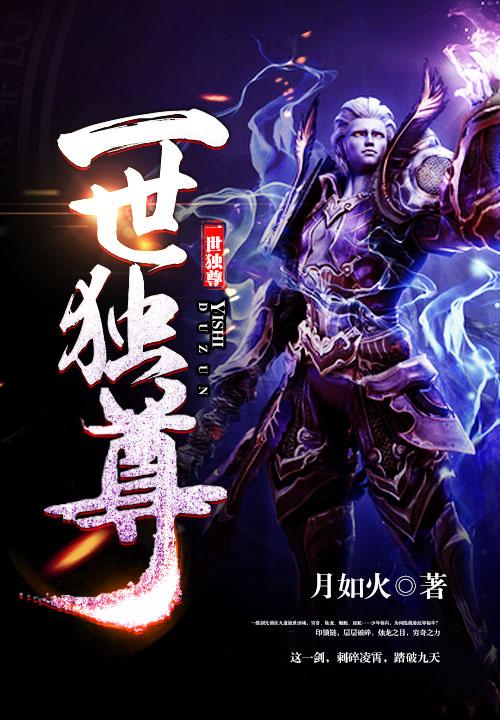秃鹫小说>祥瑞 王莽和他的时代 > 第36章(第1页)
第36章(第1页)
灌玉堂
流金门
——汉元帝时童谣
一、吕宽大案
1.孤独的汉平帝
九岁的中山王刘箕子身着礼服,孤身从中山国出发,准备继承汉哀帝留下的皇位——成为汉平帝。车驾快要抵达长安时,他留意到祖先的陵墓,如山一般高大,但并不寂寞,因为这些帝陵的脚下已经形成县邑聚落,人烟稠密。过灞桥时,他的随从告诉他,紧挨着灞桥的帝陵是太宗文皇帝的陵墓灞陵。一百八十年前,汉文帝也是以诸侯王的身份,从封国来到长安即位为皇帝。
这些“家史”箕子并不陌生,但他毕竟只是孩童。他是否知道,当年汉文帝是抱着出生入死的决心奔赴长安的,因此才会带着舅舅薄昭和多名亲信,并在住进未央宫的当晚就让亲信们接管了皇宫的保卫,又在局势稳定后的第二年把母亲薄太后接进长安。
而箕子身边只有几名随从。祖母冯太后一家在汉哀帝时期被诛灭,虽然王莽“拨乱反正”,已给冯太后平反,王氏家族和箕子一家暂时处在蜜月期,但王莽惩于汉哀帝的教训,箕子的母亲卫氏、舅舅、朝夕相处的姐妹以及王国的官员都被勒令留在中山国。他不得不依靠马车外面的那两个陌生人:车骑将军王舜和大鸿胪左咸。
此刻,箕子不知道他已经与母亲永别,也不知道自己将在五年之后死去。《汉书》最后一篇“帝纪”末尾的赞语,前八个字概括了箕子的帝王生涯:
孝平之世,政自莽出。
箕子登基后,形同傀儡。
后宫里的王政君,名义上地位至尊,但在王莽劝慰下,除了“封爵”这一事务外,不再过问其他政事。
朝廷在原来的三公之外,完善了新的制度安排——四辅,形成了“四辅三公制”。四辅即太傅王莽、太师孔光、太保王舜、少傅甄丰这四名高官,性质属于内朝官;三公还是原来的大司马王莽、大司徒马宫、大司空王崇,性质属于外朝官1。这样,内外政事分别由“四辅三公”平决,表面上看这采取的还是“集体决策”。
但大权当然由王莽掌握。因为他一身兼有四辅的太傅和三公的大司马之职,内外两任,权力牢牢抓在手里。而且四辅三公虽然各司其职,但用人这种大事必须由王莽亲自处理。班固尤其注意到,以王莽为核心形成了一个很小的圈子,他们才是真正的权力中心。
王舜、王邑为腹心,甄丰、甄邯主击断,平晏领机事,刘歆典文章,孙建为爪牙。丰子寻、歆子棻、涿郡崔发、南阳陈崇皆以材能幸于莽2。
这些人在王莽时期最为炙手可热,也将在后面的故事里频频亮相:其中安阳侯王舜、成都侯王邑分别是前大司马王音、王商的儿子,王莽的堂兄弟,故而被视为腹心,王莽很多决策先与他们商议;甄邯是孔光的女婿,甄丰是甄邯的兄长,甄氏兄弟主要负责“击断”,也就是“发难”“挑事儿”;平晏是前丞相平当之子,五经博士,负责王莽的机要;刘歆是前宗正刘向之子,王莽的旧交,负责文章,制礼作乐;孙建负责军事保卫事务,是王莽最忠实的将领。其他人,甄丰的儿子甄寻、刘歆的儿子刘棻,以及崔发、陈崇等资历尚浅,主要是对前面的“大佬”唯命是从,做具体事务。
其中,崔发是儒生,精通符命之学,早年在家乡涿郡收徒讲学,尤其对《诗经》很有研究,他大概是怀着对王莽的崇拜前来投靠,因为擅长解说符命而被王莽笼络。陈崇大概曾是文法吏,胸怀谋略,性格深刻,下手也狠,被王莽引为爪牙。
这俨然一个王莽的“小朝廷”,把控着汉廷的实权。
倘若只考虑权力的因素,王莽不让卫氏家族来长安,当然是为了独擅大权。但在当时儒家改革呼声高涨的情况下,王莽这么做自有一番过硬的道理,那就是“为人后”之义。
所谓“为人后”,就是明确一个人在礼仪上是谁的后代,继承的是谁,逢年过节要给谁祭祀。这在汉朝是了不得的大事,一个人死后倘若没有后人祭祀,那就是孤魂野鬼,是非常可怕的事情。
所以,如果一个人绝嗣,他要么在生前就收养或过继个人来当自己的后人,要么死后由家族帮忙给过继一个。过继的后代在身份上和亲生儿子无异,财产之类尽归己有,但礼仪上与亲生父母就不再有关系了。所以,箕子来到长安,当了皇帝,也就和中山国没有关系了,他的母亲舅舅一家也就不必来。
王莽把“为人后”看作最为重要的伦理,并不纯粹因为儒家确实有这份讲究,而是他认为汉哀帝最核心的罪过就是不懂“为人后”之义。如果他懂,专心尊奉汉成帝的皇后、皇太后足矣,完全不需要把自己的生母甚至祖母都弄到长安,重设名分,扰乱纲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