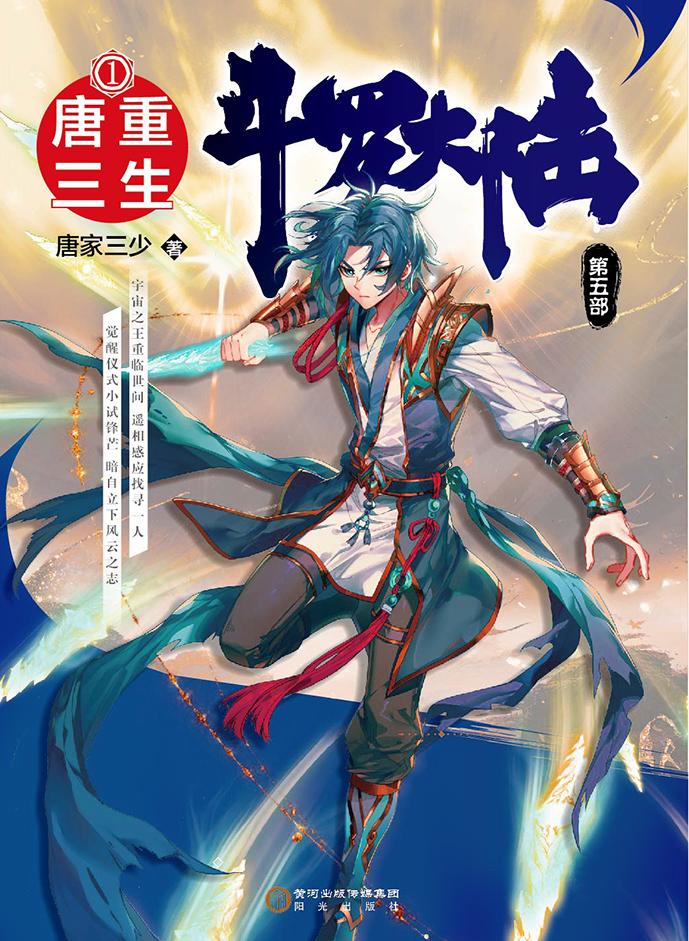秃鹫小说>和疯魔反派绑定 > 第12章(第1页)
第12章(第1页)
元旻在外静静看阿七操作,直到看她东张西望后侧身走进去,忍俊不禁,也跟着走了进去。
行了数十步,通道往下,又走了两刻钟才见光,空气却愈发浑浊,带着沉闷的土腥气,阿七解释道:「我们在珪山山腹内。」
前方已有一年轻男子提灯趋步迎来,单膝跪下拜道:「见过殿下,见过首领。」
阿七问:「天权,兰夫人可到了?」
天权回:「兰夫人已携子等候多时。」
天权带他们又走过了一条长长的丶往上的台阶,随着头顶石块挪开,清新空气乍然涌入。元旻走出甬道,发现自己身处一间猎屋,猎屋地处珪山山腰的一处深凹,周围皆是高大乔木,遮天蔽日。
「渝安云飞燕,拜见殿下,拜见七公子。」中年美妇一身绫罗丶也不介意地面脏污,倒头便拜。
云飞燕身后跟着一名十四五岁的少年,见此情状也跟着稽首跪拜,正是其子兰秉奕。
阿七解说道:「珪山酒楼茶肆繁多,客商往来信息密集,卑职便安排天权在此驻点,并安插耳目扮作伙计,分散在城中多处酒楼。兰夫人为此事操劳颇多,还在山中建了一座仓库供我们物资中转。」
「何止这些,云夫人十多年经营所得尽数投给本宫招兵买马,听说还为此债台高筑,可谓孤注一掷」,元旻欣然,「大事若成,兰夫人劳苦功高,不知以何言谢?」
云飞燕仰头,眼神坚定:「飞燕自幼好学,心存青云之志,无奈敝国女子地位低下,只能依附父兄丶夫婿丶子侄苟活,妾身多受此等苦楚。听闻敝国以东,有国名为大翊,女子也可自立宗祠丶出将入仕,飞燕不才,愿报效如此之大国,请殿下成全。」
元旻颔首应允:「往后,大翊世袭列侯将多『云』之一姓。」
兰秉奕忙随母跪拜,朗声道:「草民云秉奕,愿为大业尽绵薄之力。」
寥寥数语,弃了国籍丶改了姓氏。
阿七与天权进甬道离去,元旻忽停住,转身问云飞燕:「明珠已替夫人还了,景樊鳏居多年,毕竟是青梅竹马的爱人,夫人当真不愿……」
云秉奕也道:「母亲支撑家业丶艰辛多年,任何想法孩儿都是支持的。」
云飞燕沉默,而后坚决摇头。
元旻神色歉疚,黯然低声道:「是在下唐突了,只是同为男子,想问夫人一句,青梅竹马的情分,比不过凌云壮志么?」
话是对云飞燕说的,目光却一瞬不瞬凝视着甬道入口。
云飞燕摇头道:「恐令殿下失望,妾身先是云飞燕自己,其次才是云家女丶兰家妇丶秉奕之母,最后才是侯谦青梅竹马的燕燕。」
。
二十年前,官家子侯谦与商户女云飞燕青梅竹马丶私定终身,时年十八岁的侯谦在雪中跪了三天两夜才换来父母应允。两家已过纳徵之礼,侯谦之父却因犯颜直谏被当庭杖杀,阖族流放。
当年,为他散尽千金四处打点的是她,孤身去流放地找寻的是她。
找了两年丶等了两年,云父突发恶疾过世,母亲软弱丶弟弟年幼,为保住云家产业,身为长女的飞燕遵循父亲遗志,嫁入兰家。
知君用心如日月,事夫誓拟同生死。还君明珠双泪垂,恨不相逢未嫁时。
十年后,一名叫景樊的书生崭露头角。又过了六年,景樊已成为一州刺史。
她有一次携子归宁,途径金阙,被恭恭敬敬请入刺史府,那人身形已变丶容颜已衰,却仍用熟悉的语调,颤声唤她:「燕燕。」
十几年的光阴隔在他们中间,一去不返。
徒羡梁上双飞燕,不许人间共白头。
云秉奕看着一行人消失在甬道后,恻然道:「母亲何必如此自苦?」
云飞燕叹了口气,笑道:「奕儿,你记住,一辈子只能往前看,有些事过了就是过了,就算因一点痴念找回,也早已面目全非。」
当年,夫婿亡故丶幼子嗷嗷待哺丶娘家无兄弟支撑,夫族如狼似虎。那段最黑暗的日子里,她甚至想过抱着幼子从高楼跳下,一了百了。
在那个被恐惧焦虑灼得无法入眠的夜晚,房间里突然出现一个玄衣男子,风帽遮住他大半张脸,只看得见煞白的下颌肌肤丶毫无血色的嘴唇,那人悄无声息地坐下,毫无起伏的声音丶包含着无法抗拒的蛊惑:「交易么?」
「我帮你扫除障碍,扶持你在兰家站稳脚跟,甚至可以做得更多,而你…」,那人似乎笑了笑,「待你家业稳固,我自有安排,你只需记住,手持此玄色凰羽者,便是你未来的主上。」
前有豺狼丶后有秃鹫,已入穷巷,不如放手一搏。于是她眼一闭,心一横道:「我答应你的交易。」
相安无事过了十几年,家业逐渐壮大,那个肌肤煞白的男子却再也未出现过,有时她甚至觉得,那是自己在绝境中产生的幻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