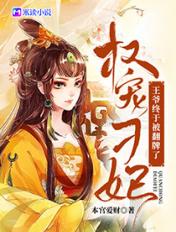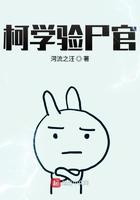秃鹫小说>攻略未婚夫的门客重生 > 100110(第2页)
100110(第2页)
“我说话管用吗?”徐复祯有些怀疑。
“当然有用。”霍巡微笑道,“你把改革的方向往旧党的利益上引,譬如让钱得权,他们会唯你马首是瞻的。”
徐复祯不明白:“改革的利益还是给旧党,那不是白改了吗?”
霍巡忍俊不禁。成王的势力主要还在西川路,借由改革可以充壮实力;而徐复祯现在代表的就是京城旧党,她倒是一心一意地替他们打算起来了。
“你放心。”他笑着说道,“最终怎么改,还有一番拉扯。只是不能白白把时间浪费在改不改上面。冬天一到,外族就要入侵了,二十几个边地重镇等着徐姑娘你一句话呢。”
徐复祯顿感责任重大,被他一番点拨,又有了方向,因此恨不能立刻回去把那些奏折都批复了。
正好这时小皇帝又重新进来了。徐复祯虽然愿意跟霍巡待在一起,可眼见还要再讲半个时辰书,他讲书的时候也不会看她,干脆便宣可喜进来看着,自己却回昭仁殿去了。
她细细看过那些奏折,又研究了一回如今的国策。遴田令刮尽民膏,收上来的税银被权贵层层瓜分,如今要一下子拿出四成给地方支配,权贵旧党自然是不愿意的。
可是,税银给地方长官拿着,他们也未必全部用来充缮军民。
霍巡说的让钱得权不无道理,如果在各路多设一位监察使,由中央指派,这样既能加强皇权对地方的控制、平息旧党对改革的抵触,也能在层层盘剥中省出军需来御敌。
她打定主意,便写了一张奏拟送到太后那里去。太后也看不出好坏,便宣周诤进宫商议。
徐复祯病愈后第一次见到周诤,她从前只听过枢密使的大名,却从未见过他,难免有些紧张。
没想到周诤对她倒是极为礼重,还关怀了一回她的病情,又说周家给她送去了两支老山参,问她可有收到。徐复祯有些受宠若惊,连连谢过他。
周诤倒是纳闷起来,这小丫头平时见到他都不假辞色,怎么病了一回倒是礼貌了许多。可她越是客气,周诤反而越是疑心起她的能力来。
直到他看到徐复祯的奏议,眉头渐渐舒展开来。枢密院本就掌着各路军队的调令,这番改革加上一个监察使,于周家的利倒是远大于弊。
周诤立刻拍板同意了。
太后于是让徐复祯拿这张奏议去找彭相商量,言外之意还是让她说服彭相。
徐复祯心道:太后可真看得起她。彭相是百官之首,连她姑父递了拜帖都未必能见到的。能听她一个小姑娘的话吗?
可是太后发了话,她也只好硬着头皮去了一趟值房。
各司衙门每日会派一名官员在值房当班,而彭相则是日日都在。可徐复祯根本不认识谁是彭相。
她站在值房门口踌躇了一会儿,看到里面分坐着一群神色整肃的官员,不免紧张起来。
这时有人注意到她,竟然纷纷上前朝她见礼:“听闻前些日子徐尚宫病了,如今可大好了?”
徐复祯并不认识眼前的官员,只好含糊其辞道:“蒙大人吉言,好多了。请问相爷在哪?”
那官员一面捋须笑,朝着北向写着“恪恭首牧”的匾额一指,笑道:“那不是?”
徐复祯望过去,那匾额下方的桌案前坐着一个两鬓生霜的六旬官员,绛紫色仙鹤补的官服给他平添了几分威肃,此刻正抬头看向她。
徐复祯连忙走过去,还未及向他问好,彭相先开口道:“徐尚宫回来了,快请坐。”
徐复祯一愣。枢密使和宰相是文武官员之首,怎么都对她这么客气?她依言在桌案对面坐下,朝彭相呈上了那纸奏议。
彭相接过去看了,眉头紧锁着。徐复祯觑着他的神色,心里不由紧张起来。她也不知道这番奏议能否说动彭相同意推动改革。一会儿彭相要是发难,她该怎么应对呢?
许久,彭相终于缓缓问道:“这是你的意思,还是枢密使的意思?”
徐复祯下意识道:“是我的意思。”
话一出口她便后悔了。倘若说是枢密使的意思,说不准彭相就同意了。毕竟,周诤看起来比她可靠多了吧?
没想到彭相将那纸奏议收入袖中,道:“知道了。此事明天早朝再拿出来议。”
徐复祯没想到他那么轻易就同意了。直到从值房出来,她还是如在梦中。怎么感觉好像一点难度都没有啊?
有了这一战的告捷,又兼见到了霍巡,她对宫里的抵触倒是少了很多。
次日早朝,议题还是税赋变革一事。旧党一改之前不可商量的态度,同意推动改革。
同时,又提出了要将那四成税银收归中央后,再由相府拟令、户部拨放到地方去;同时,每路要另设一名监察使来分管这部分税银,也是由相府任命、吏部派遣。
这样一来,那些银子不过是左手腾右手,依旧掌控在旧党手里。以成王为首的新党自然不能答应,众人又开始争论起来。
徐复祯坐在殿台上,在一众朱紫朝服的官员中搜寻霍巡的身影。
有两次她和他对视上了眼神。徐复祯朝他微笑,他却视若无睹地转开了目光。
徐复祯心想:该不会是改革的条件开得太狠,他不高兴了吧?可是,那明明是彭相的主意。霍巡会迁怒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