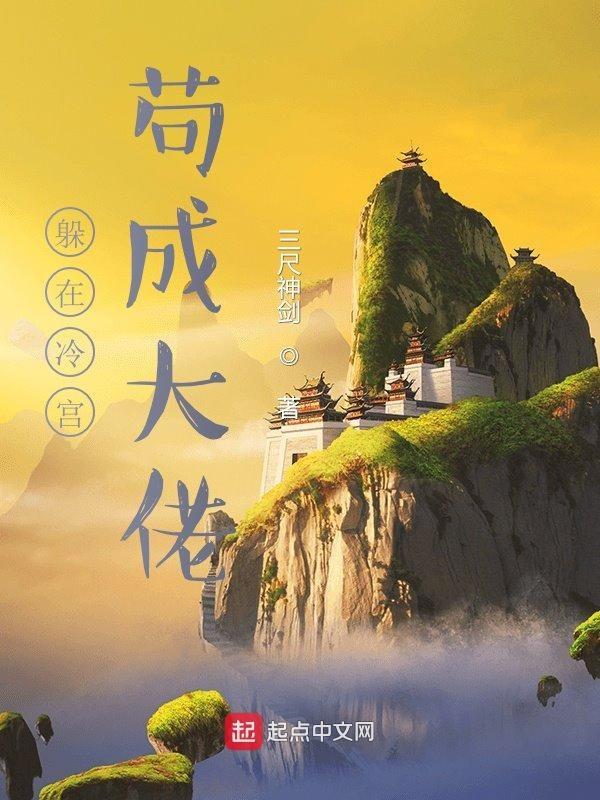秃鹫小说>重生后独宠灾星小夫郎23 > 2230(第4页)
2230(第4页)
“喂,前面的,你的市金呢?没交齐就想溜?”
钟洺向前没走几步就被人叫住,他回头看一眼。
小吏比他矮数分,令人不得不低着头,场面怪滑稽。
他提了提手中木桶。
“我不摆摊,这些是给食肆送的货。”
小吏怀疑地打量他,同时暗恨这傻大个怎能长如此高,吃什么长大的,遂态度更不佳。
“哪家食肆,掌柜姓甚名谁?”
“四海食肆,辛掌柜,他三日前在我这里买了龙虾,还给了一百文定钱森*晚*整*,官爷若不信,尽可去问。”
见他说得头头是道,该是做不得假,四海食肆又是乡里老字号,小吏磨了磨牙,有些不甘心地给他放行。
钟洺面无表情地转过身,恰逢身后的小吏又朝后面的人吼道:“不过五文钱罢了,你们这些人得钱多容易,下海捞一把就有,五文钱也不舍得掏?回头市金涨了价各个就老实了!”
小吏恶声恶气,却不知自己一句无心的话提醒了刚刚过去的汉子。
钟洺一下子记起,涨市金这事先前当真发生过,就在不久之后。
原本五文的市金一夕之间涨作八文,只对水上人收取,其余摆摊的乡里人、村户人,照旧是五文。
别看只是多了三文钱,一个月下来,可就是足足二钱多银子。
而眼下在乡里街旁赁个摊位,只要不挑拣地段,一个月的赁钱也不过二百文,且不许贱籍租赁,加钱也不成。
最重要的是,伴随市金上涨,乡里还开始对上岸贩鱼获的水上人加收鱼税,鱼获按斤称重,每斤加收一两文不止,赶上一眼就看得出的值钱货,譬如龙虾、海参、石斑等,还会漫天要价,狮子大开口,全看当日小吏的心情。
不想交,也可以,赁个摊位即可,本朝商税原本就只针对于有铺面的坐贾征收,零散摆摊的小贩不在其内。
这就导致问题又绕回最初,水上人是贱籍,赁不得摊位。
种种条框,明摆着就是冲着多刮他们一层皮来的。
硬壳子的海产压秤,有些一斤压根没有几个,水上人多了支出,卖价只能也跟着涨,惹得乡里人同样不忿,整个九越县怨声载道。
这正是钟洺下狱前夕发生的事,那会儿他得了消息后,还特地回白水澳告知二姑、三叔几家子族人,建议他们提前找找门路,在城里合赁一个摊子,不然以后靠贩鱼得的利只会越来越少,到头来只肥了官差的荷包。
可当时他“名声在外”,族人岂会信他。
得知他因要找门路,打点上下难免还要花钱财时,还说他是不是在乡里沾了赌瘾,亦或养了粉头,赚的抵不上花的,回澳里打起亲戚的主意,开始招摇撞骗了。
钟洺觉得失望,撒手不管,没多久他蒙冤坐牢,想必当日打定主意不信他的人还庆幸得很。
……
现今旧事重演,既这一回他打算脚踏实地经营日子,不管别人,首先自己赁下个摊子才最紧要。
于是将此事暂记下,盘算一番。
钟洺很快离开了喧嚷的码头圩集,拐了几个弯后,在与苏乙说好的一家铁匠铺子附近找到了人。
小哥儿把扁担放在地上,整个人贴着墙根站着,灰衣几乎和乡里常见的蚝壳房的外壁融为一体。
不仔细看,险些错过。
钟洺上前,语气是自己难以察觉的温和。
“等多久了?”
“没多久,我也刚来。”
苏乙其实已经早就来了乡里,已在圩集上零卖了些虾酱,而后赶早两刻钟到了此处。
他怕钟洺比自己更早,自己等对方,总比反过来要好得多。
钟洺轻轻颔首。
他之所以和苏乙约在这里见面,是因为这附近少有水上人来往,且他还在铁匠铺子定做了铁器。
“你略等我一会儿,我去对面铺子取样东西。”
他叮嘱一句,小哥儿自是答应。
进到铁匠铺子,他提了一嘴要取的物件,拿出上回伙计予他的纸条,伙计接过,对着上面鬼画符一样的记号,送来他几日前来此定做的几根细长铁签和配套的箭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