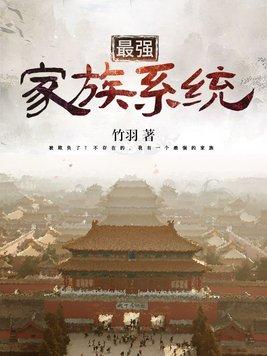秃鹫小说>bl中短篇推荐 > 第20章(第1页)
第20章(第1页)
铁男一定是这样!绝对!
现在问题来了:自己是铁男的朋友吗?自己懂过铁男吗?如果一定要互相理解才能算朋友的话……
一支车队放着巨大的噪音从他身边穿过,三井寿退开半步嫌弃地在鼻尖位置扇了扇风。机车群的尾气味道真叫人恶心,当初居然还挺喜欢,多不可思议啊。
他已经很久没见过暴走族了。现在的少年有着与他少年时不同的审美观,暴走族已经不是成熟和酷的标记。听德男说,家乡的暴走族也少了很多,机车越来越回归代步属性,半夜跑出来插着旗招摇的人已经成了老古董。
听到这些话时,三井寿真想再问德男一句,这几年遇见过铁男没有。但他到底没问。其中缘由衆多,比如都过去了他不想提那格格不入的一年,比如他其实有所愧疚因为对铁男不够义气。
而他心底藏得最深的那份坦诚让他知道,还有一条原因:即使面对德男这个多年老友,他心里仍有一块不想拿出来分享的世界,不想让自己完全坦白。
如果一定要互相理解才能算朋友——夜风吹起悲凉,三井寿心酸地发现,只要定义得够狭义,他就没有朋友了。
他国中期的队友拿他当偶像,他理所当然享受他们围着自己转。他的不良期的朋友连他为什麽不良都不知道,他则简单的以为他那些不良朋友天生不良。他与高三的队友之间从不涉及稍微深入一些的话题,他们是球场上的战友,但从来不是贴心的朋友。大学之后,他更是独自承担心事,无论同学还是职场上的合作伙伴,都保持着互相尊重的大人之间的社交。
青春褪了色,格格不入与浑然一体都成了老照片,昏黄模糊了分界,一起丢在过去。现在,他是个只能哭给自己看的大人了。这件事值不值得哭一场?
那他从前认识的那个撞进三井的青春里的大人呢?铁男有没有在发现无人可以依靠时候哭过?
自己真想过铁男在想什麽、想要什麽吗?做朋友应该想的吧!理解应该是相互的吧!任何一段平等的关系里都应该良性互动吧!所以自己其实没有朋友吗?
这不对!必然有错了的地方。
站在街头的三井寿把自己问得心浮气躁,对着半边月亮发脾气。霓虹几乎全灭了,街灯一枚枚枯燥刻板地尽忠职守,驱赶最漆黑的夜。
他选了一枚路灯,将自己留在光晕里。不必问为什麽,也不必问哪一枚,都一样。他需要一点光,让他安全、不迷失。
他需要光,于是有光。他需要朋友,于是有朋友。他是男主角吗?拥有光环的男人,世界的中心,这个故事里没有他便成了一捧随风而散的灰,别人都是给他当配角的npc。
三井寿双手支撑住路边护栏,仰起头,在白光里望着灯泡做了两个深呼吸,吸到满鼻子初夏的夜来幽香。路灯们乖巧的排列着,向两方伸展,光圈越远、越小、越不清晰。但他知道,那里的灯其实和他头顶这枚形制相同、亮度相似。
就算他为人再怎麽狂妄自大,也不至于真拿自己当世界上唯一的男主角。最多在自己和屈指可数的几个人的人生里当主角罢了。
耳边突兀地响起汽车鸣笛声,刺透幽静深夜。三井寿吓了一跳,从护栏,跳下,瞪着计程车司机。
“去哪儿?”夜班司机招揽他的生意,带着笑。
铁男从前也常这麽问三井。那时铁男会收起平日的半笑不笑,问得懒懒散散,随三井想去哪儿就去哪儿的便。
原来铁男是计程车吗?三井寿把自己逗笑了。时隔多年之后,他领悟到铁男的本质就是没有本质、铁男的意义就是毫无意义。
这晚上,三井寿梦见了铁男。
最开始他不知道是梦,他们在湘南,在街上閑逛,当年他们最寻常的杀时间方式。铁男走在他身边,叼着烟。他走在铁男身边,穿着铁男的背心。街上的背景清晰得过分,他甚至看见了风。
风是亮晶晶的,像明明晴天有太阳却偏要飞一阵的极细密的雨丝,区别在于风横着飞。
他觉得有趣,回眸问铁男看见了没有。
铁男穿了一件驼色圆领t恤,半笑不笑地说当然没看见,风是无色无味的,只有脸皮知道。
他不高兴了,因为铁男不肯顺着他说。他伸手抓了一把风,可再张开手,手中空空。他只好挑剔别的事,“铁男你穿驼色太丑了!你肤色那麽深,适合穿蓝色系,显得白些。”
再回眸,铁男换了身灰蓝连帽卫衣,很像自己高一穿的那套。他开始觉得不对劲,铁男怎麽能穿他的衣服?从来只有他穿铁男的!
他又挑剔,拧着眉毛恶狠狠地嫌弃,“多大的人了你穿连帽卫衣!拜托你成熟点!”
一个眨眼之后,铁男换了白衬衫和黑西装,笑得歪歪斜斜,问要不要陪成熟的人一起去看看真正的风。
三井寿知道自己做了梦。铁男怎麽可能穿西装,铁男只适合胡子拉碴地穿背心,只适合嘴角勾出若有似无的嘲笑。
好吧,天冷时许他套上牛仔夹克。装进夹克衫里的男人还是必须嘲笑着一切的无意义,除了看风,真正的风。
这才是铁男不肯戴头盔的原因吧,感受就是意义。
人在察觉到梦时就快醒了。三井寿舍不得醒,想再沉进去,捧住铁男的两颊,贴近到眼中只有那张被风雕刻的脸,遮住提醒他正处在梦中的换装游戏。
梦不由他。
醒也不由他。
东边天际热烈如火。
三井寿远眺着霞光,突然察觉,这是这麽多年他第一次梦见铁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