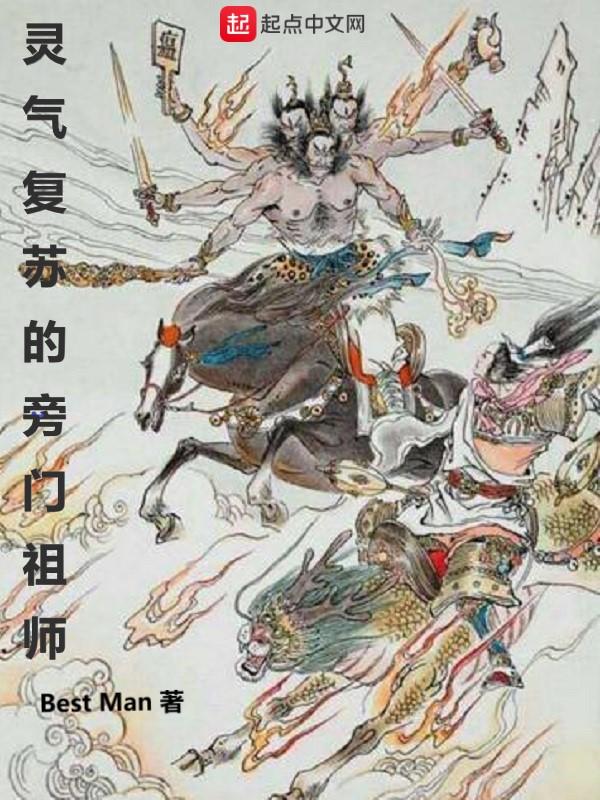秃鹫小说>被迫在永夜世界当火烛大佬 > 22不要难过(第1页)
22不要难过(第1页)
兰秋年这些天不是白东转转西转转的,尽管记不住所有那些零碎繁杂、拗口难记的地名,但至少不会离了地图就找不着北。狄敬章发来的坐标离他不算远,兰秋年脑中迅速描绘出一条曾经走过的捷径。他脚步轻巧,穿过几条熟悉的小路,居然顺利地接近了目的地。
到达约定地点,兰秋年在人群涌流中第一眼看见狄敬章——身量高拔,体态又端正,站在墙前腰背笔直,很蘸眼。
狄敬章今天换了浅色系修身毛衣来穿,和往常略显刻板的硬布训练着装很不一样。虽不算华贵正式,但能看出料子上好、将整个人衬得很好说话。他目力好,隔几十米就发觉了兰秋年的到来,心上横着的那道静弦就荡了一荡。
昨日容世群在任务群里问他们今天谁有空带兰秋年做一回课前研讨,聂舍没回话,狄敬章的设想中贺句芒本应不留情面地跳出来拒绝,但不想这大少爷竟也安安静静不作声。
如同直觉,狄敬章不禁揣测起两人的想法——想等着这差事没人接,容世群一个一个地定向询问,再不甘不愿、不丢份子地接下。不是他心思阴暗,狄敬章不得不承认,无论别人此时心里怎样,他自己确确实实就是这样想的。
所以——
“明天我训练不多,可以去。”狄敬章发送一句话过去,口吻妥帖,谁来都挑不出毛病。
容世群对他也放心,端方正直、一心训练,看着好相处其实距离感最强,既不会对兰秋年有所企图,也不会像气性惊人的贺句芒那样对译使造成威胁,于是当即就欣然把这事全权交给他。
他倒是不想想,狄敬章什么时候变成个乐于助人、紧着往身上揽活的性子了。
“狄敬…同…狄同学,”兰秋年走到近前,停住脚步,一时不知道怎么称呼,吞吞吐吐嘴里磕巴几下才略带不自然地招呼,语调带着未经红尘磨扫的生涩。
虽然他和狄敬章说过话,对方也帮过他,但不熟就是不熟,对待不熟的人时如何平衡礼仪和界限,是兰秋年苦恼已久的问题,这还是脑筋急转才想到个勉强算正式的称呼。
他那点含混不清的为难被狄敬章听得真切。
狄敬章眼底光色一闪而灭,仍是那张周道又张弛有度的笑脸,眉尾却一抬,嘴角的弧度有些微乎其微的偏差,犹解倒悬地接过话说:“你来了?”
“今天的研讨不用太在意,我们去场地后还会分配来两个组员,如果不想和他们说话就自己统计数据。”
这是个好的解决方式。
兰秋年紧张感消去不少,对这个名为“研讨”的高档东西有些好奇,道:“好。你知道我们等等要讨论什么吗?”
普通学生是不会提前得知题目的,大家都要等到达现场后再进行统一领取,顶多有笼统的区域可供预判。但狄敬章不是普通学生,他是极个别突出分子——这里的“极个别”和“突出”都是褒得不能再褒的褒义词。
能与老一辈科学家你来我往地论道,狄敬章无疑处于学术领域的头部,暸望塔科学院的大手就很遗憾他走了驻防这条路,恨不得一指头给他戳得调过头、一心扑向科研事业。
连今天的研讨会题目都是从他提出的题库里抽的,狄敬章怎么会不知道。
但他故意不明说,就眉头略紧地看着兰秋年,看那眉眼平和甚至微带宽纵的样又不是大公无私地坚决不泄露,也许求一求是很有希望的。
兰秋年哪看得出他的微表情,心觉自己让对方为难了,顿时耷下眼睫表示自己收回刚才的话。
他真不问了?
狄敬章先不解,又立马豁然,这发生在兰秋年身上再合理不过,对方本就是不太懂得人情世故的。
不懂也好。
“薪塔防护措施的修缮。”狄敬章目光柔化了一瞬,不知怀抱着何种想法开口道,“没说不告诉你。”
兰秋年彻底晕了头脑,像个系统运转速率过大导致超载死机的小机器人,他先咬字清楚地道了谢,又暗暗回想狄敬章是哪里流露出了“可以告诉你”的意思。
人类社会这套处世法则,他到底要多久才能学会?多久才能摆脱时刻碍口饰羞的窘地?兰秋年和山野灵尘中饮雨吞风的小动物一样,凡事首先凭直觉,用先天的感应去应对危险。兰秋年总告诉自己不必在意,但每面对这些洗礼泼深的、熟练的“人”时,心里那点失措骗不过自己。
狄敬章的眼神凝结在兰秋年鎏亮的发泽与白缎衣角上,身高的好处这时又显现出来——兰秋年不抬头就无从发现。午时阳光清翯翯笼着,纯白的衣襟上披满细若薄纱的晕影,赤橙光线中显出淡蓝的质感,像融化进酒水里的蓝玻璃。
仲夏天气,狄敬章无端像大饮一口maitai,连喉头都有清甜的微凉。
两人结道向研讨地点走去。
“你今年几岁?”狄敬章捡了个话题,将凝胶般的氛围缓解开一二。
兰秋年不假思索:“二十岁不到,应该还没过生。”
应该?狄敬章抓住这个不确定性很大的词汇,记不住自己生日的人,哪怕在几十年前最黑暗无望的年代应当都是少有。
“你比我们这届小一岁。”狄敬章说。
兰秋年点点头,也想问对方几个问题,“为什么我一定要进你们这个寝,三个s级还没把握守好009灯塔吗?”
狄敬章一直都觉得这安排扯到天际,他在最初坚决抗拒过,现在…就不太坚决。
“暸望塔给的说法是让你辅助我们作战,实际上我对此并不认可。”狄敬章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