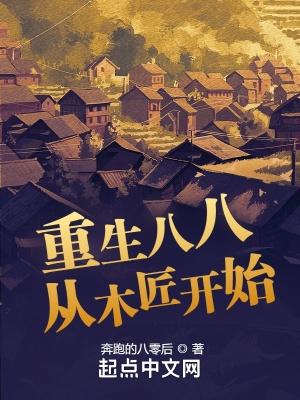秃鹫小说>拯救-deliverance- ch.1~12章 > 第三章 金子(第3页)
第三章 金子(第3页)
“你为什么看起来比我还要痛苦呢?”我轻抚过他的脸颊,划过他眼底那些坚定而破碎的眸光,“你不该比我还痛苦,这是一种浪费。”
“如果我可以替你分担千分之一的痛苦,”他抓住了我的手,“我会这么做的。”
“可是我没有一千份的痛苦。”我平静地说,“不要给你自己套上想象的枷锁,塞德里克。尤其是为了我,这不值得。”
他越发攥紧的手告诉我这话完全没有起到宽慰的作用,我叹了口气,没有抽回来,如果他需要握着我的手,那就让他握着吧,“有的人出生即夭折,有的人天生残疾,有的人终其一生都在炮火中流离。如果你为像我这样的小事悲伤,你会被这个世界的悲伤压垮的。”
“你都是这样告诉自己的吗?”他问,我静静地回视他,“因为这世上有更值得悲伤的事,所以你的悲伤无足轻重。因为这世上有其他更值得哭泣的事情,所以你不应该哭泣。”
“不然你会同时被自己和世界的悲伤压垮。”
那双蓝灰色的眼睛像波光粼粼的湖面一样对我闪烁着、低语着,好似有万千情愫可以诉说,可我选择移开了视线,“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
塞德里克忽然笑了。
“听不懂也没关系。”他垂下了目光,指尖缓慢地摩挲过我的手背,如同在谁的心上划过一道温热的痕迹,“但我仍然会告诉你。”
“我会告诉你,不要那么自大,林小姐,你不是唯一一个对这个世界有标尺的人。”接收到我无语的眼神,他轻笑着继续道,“我也正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我有自己的眼睛,也能判断一切值不值得。”
“比如,我会说,”他停顿了一下,直直地望进我的眼睛里,“会为这个世界哭泣的人,也值得有人为她而哭。”
在月光下有永不褪色的东西吗?当月亮统治了黑夜,为黑夜慷慨地落下一层明亮而澄净的白纱,世界到底是融化在月光下,还是仍然反射自己的色彩?
也许我至少为自己找到了一样永不褪色的东西。
金子。当塞德里克在湖水般的月光中对我微笑,我想。
金子是不会在月光下褪色的。
*
不同于圣诞,学期末的返程列车和开学时是统一的,都在上午11点出发。我不会说我对于第一次登上霍格沃兹特快没有一点兴奋,毕竟虽然路程将近七个小时,但据说沿路的风景还是不错。为什么直到现在还是“据说”呢,因为其实我还是一点风景都没注意到——
“不要再表现得像个过度保护的老母鸡了,塞德里克·迪戈里!”我第十次嘶嘶地重申,“我说过我可以一个人到破釜酒吧登记入住!我告诉你那些孤儿的身世不是为了让你同情或低看我一眼!”
早知道我会在特快上和塞德里克像这样纠缠不休地争吵,还不如真的做个吉祥物被其他赫奇帕奇抱着庆祝一路算了——没错,邓布利多真的十分厚道地为我那象征性的救援给赫奇帕奇加了二十分(虽然那仍然不足以改变赫奇帕奇垫底的事实)。
“这和你的经历无关。”塞德里克压低的声音仍无半分退让的迹象,“因为在你口中‘一个人’的意思就是一个不满十五岁的未成年女孩!”
“天啊,所以多一个不满十五岁的未成年男孩会大大增加我的安全性是吗?”
“我可以请求爸爸——”
“不。”我一锤定音,不容置喙地直视着他,“我不是在征求你的意见,塞德,我是在通知你。我可以自己做决定,下车后我要一个人去对角巷。”
他没有避让地回视着我,紧抿着嘴角,胸膛轻微的起伏表明他刚刚交换了一个隐蔽的深呼吸。
“唰——”突兀的拉门声打破了剑拔弩张的空气,头一个揣着零食进来的麦克一触到我们转头的眼神就假心假意地呛咳了下,“梅林的破洞长袍!这里是刚刚进行了一场决斗吗!是我的错觉还是你们吵架越来越频繁了,麻烦进入下一个冰川冷战期之前提醒一下我们这些无辜群众好吗?”
第二走进的艾比也紧接着就挨着我坐了下来,来回扫视了一下我和塞德里克的表情。
“怎么了吗?”她把被拜托的南瓜馅饼塞到我手里,紧张地小声问。
我瞥了一眼塞德里克紧绷的神情——下一秒就卖了队友。
“显然不知道为什么,”我恶狠狠地啃了口馅饼,“我们的赫奇帕奇之光今年放着好好的家不回,硬是要在下车后跟我一起到破釜酒吧。”
果不其然此话一出,三对不解的视线都投向了塞德里克。他深深地叹了口气,“我从来没说过不会回家,我只是想送你到那儿。”
三双眼睛又转向了我,“有什么必要吗?过去两年都是我一个人,难道我现在不是好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