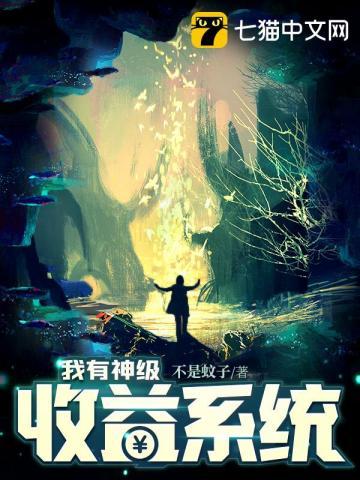秃鹫小说>死对头他总想和我结婚笔趣阁 > 第95章(第1页)
第95章(第1页)
他把徐心诺抱在怀里确实没有喝酒但是酒不醉人人自醉。今天这一晚上庄逢君跟着听了许多关于徐心诺的个人隐私问题有些是他知道的比如内裤喜欢什么颜色很无聊但是他竟然都清楚有些是他从没听过的比如初夜还在不在初吻又是跟谁如此等等。即便一直告诫自己都是过去式不需要较真庄逢君还是不免竖起了耳朵甚至有些紧张地等一个答案然后听见徐心诺说初吻是跟他家以前养的一只虎皮鹦鹉。那些朋友便起哄没有人相信。在座除了庄逢君信他能干出这种事情庄逢君还知道那虎皮鹦鹉就是许云富养的那只于前两年的冬天寿终正寝。那人呢?徐心诺又不傻他把这个答案糊弄过去了。庄逢君自认他不在意这些又不是什么满清遗老到这个年代谁还在立贞洁牌坊结果还是——去他的不介意他就是比别人有理由生气气自己过去的七年里没看好徐心诺。原本他有机会陪在喜欢的人身边分享每一个美好的时刻可时光那样无情一转眼就都错过了。大概让庄逢君尤其不能忍受的是徐心诺要是非要眼瞎的话还不如直接来找他!人只要情绪上头总是容易冲动行事。总之脑筋一热就亲了下去一时冲动但并不后悔。既然挑破了窗户纸再装下去也没意。庄逢君目光灼灼去找徐心诺的眼睛。徐心诺一跟他对视便被灼伤了下意识挪开视线天上地下到处游弋。他的眼珠子咕噜乱转不知在想什么东西睫毛也跟着忽闪又黑又密痒痒地扫在庄逢君心坎上。“诺诺。”庄逢君喊了他一声“你看不出来吗?我想追你我在追你。”!“啊。”徐心诺手脚不知道往哪往,也不知道说什么,“谢谢?”“我知道,这有点突兀,你可以慢慢考虑。”庄逢君犹豫着,终于还是,一点一点松开徐心诺,他抬起手,给徐心诺整理了一下卫衣帽子,画蛇添足地试图把帽子扯得更对称一些。“不急,你先想想吧,以后再给我答复。”庄逢君放下了双手,轻轻叹了口气。他的声音里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紧绷。其实在庄逢君的预想中,他在有朝一日表白的时候,应该也要掌控着所有节奏,甚至这里,他还应该开玩笑地调侃一句:“二十四个小时够吗?”好推动徐心诺一把,让他赶快做出选择,认清谁才是自己的良配,结果事到临头,根本无心开玩笑,只剩下一个想法。他也会害怕遭到拒绝。接下来的气氛变得有些僵硬,因为谁都不再说话。徐心诺倒是想说点什么,但他的脑子里像被灌了十瓶浆糊,黏黏糊糊不成体统。庄逢君把卫生间让给他洗漱,徐心诺全靠着肌肉记忆刷了个牙,心不在焉地把牙膏挤到了洗脸盘里,刷牙时又咕咚吞下了一大口漱口水。有朦胧的猜测是一回事,把一切挑明又是一回事。他不知道怎么形容自己的心情,但这种不可描述的情绪在走出卫生间后又高涨一截。徐心诺看见庄逢君坐在客厅沙发里,像一樽沉默的雕像,没玩手机,没开电视,只是安静地坐在那里沉思。客厅里只开了两盏壁灯,并不明亮的暖黄灯光打在他身上,勾勒出比平时更加立体深邃的光影,鲜眉亮眼,舒舒郎朗。庄逢君的外型总是很好看的,无可挑剔。徐心诺也不是小孩子了,就在之前,他还把求偶这件大事列在日程表里,如果在酒吧或哪里遇到这么一个天菜,不管是发展一段关系还是一段露水情缘,他想,那肯定都是不亏的。又如果他是被一个外人表白,要考虑的问题就简单很多:喜欢就答应,不喜欢就拒绝。男朋友么,无非就那么回事,交往一下试一试,不好就扔,上一个徐心诺就这么干的。他那么年轻,初生牛犊不怕虎,就算不幸遇到了垃圾也无妨,毕竟试错成本很小很小。可问题就是,这不是外人,这是庄逢君,是不太能随便对待的一个人。徐心诺除了喜欢益智玩具,还很有动手精神,因此他的小时候,家里的闹钟、手表、收音机……没有不敢动手拆的东西,拆完了再装回去,总会多出几样零件,而大部分的结果,就是好好的东西因此祸祸坏了。东西被弄坏了,最多挨一顿揍,再不济还可以去买个一模一样的。这会儿徐心诺却怂了。他却不敢用这种随意莽撞的态度,像拆闹钟一样去拆解他和庄逢君的关系,再不计后果地组装起来。毕竟他们的关系太密切、结构太稳定了,这种花了十几年时间培养出来的情谊,不是可以随便祸祸着玩的零件,去哪家商场也不可能重新再买一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