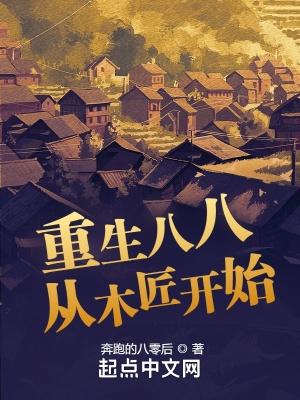秃鹫小说>一如既往的默契什么意思 > 第65章(第1页)
第65章(第1页)
“这座城市有时候糟糕透顶,不是吗?”
“我不会说出去的。”莎拉说,“但你最好别跟别人谈论关于这方面的任何事。”
“我会的。”说完,女人捂着脸不知道在想些什么。莎拉依旧在嚼着饼干。
长达两分钟的静默后,琼·巴托洛平静地说:“萨列里阁下是他的教父。”
白日比莎拉·马里诺想的要漫长。她从琼·巴托洛的殖民地风格别墅走出来,一路步行到电车站,红砖块的建筑已经被层层迭迭的树遮挡,看不见了。她在中心岛市区下车,沿着威尔逊大街漫步。
穿着长袜和猫跟鞋的一双腿从车座上伸出,轻巧地踏在马路沿上,用鞋尖点着地,不用把脖子伸进车里看都能知道车主的脸定是在漫不经心地打量着街上的行人。包包的挂链发出响声,女人站起来了,精致的金色盘发被镶着宝石的金属盘口固定,几捋卷曲的刘海垂下。她四处张望,然后往电影院的方向走。莎拉在女人后面走着,看着女人晃动的耳坠,珐琅彩的,她想,琼在萨列里阁下的家宴上带过,很漂亮,我也该买些新的首饰了。她们随着人群走到了帝国大厦门口,女人停下来了,翻弄着自己的包。莎拉跟着一起停下,不带情绪地望了一眼女人,准备绕过她走。
刚迈出一步,七点钟方向通天的巨响挤压着莎拉的耳膜,如钢板从天而降砸到另一块钢板上,所形成的屏障隔绝了其他一切的声音。心脏咚咚地跳动,莎拉像是机械木偶似的转过身子,再僵硬地转过头。
映入她眼帘的是一个姿势扭曲又安详的金头发男人,车顶被他砸的凹陷下去,挡风玻璃从摔得稀巴烂的脑袋底下裂开,血溅到旁边,其余的沿着裂缝流下。
男人惨白的皮肤和金色的头发在楼宇间射进来的太阳光照耀下闪着不正常的光辉,他怒目圆睁,用快要从眼眶中崩出的双眼谩骂着没有对此感到悲悯的天空。
走在她前面的年轻女人被眼前触目惊心的场面吓得女人腿脚发软,她颤颤巍巍地往后退,却脚底一滑,眼看着就要失去平衡时,胳膊突然被人拽住,莎拉扶住了她。她回头看了眼莎拉,转过头看着命案现场,手指哆哆嗦嗦地指着车上的人,嗓子像是被人卡住了,抖动的脑袋像是充满气体的茶壶,滚烫的蒸汽在口腔中回旋,最终,她恐惧感的具象在鲜红色腭垂的摆动下发出刺耳的尖叫。尖叫的恍惚间莎拉牵起女人的手将他拉走,但女人的小腿肚发软,没走几步就重重的跪在地上,差点把莎拉连带着摔倒。两人都听见了布帛崩断的刺啦声——女人的裤袜从左腿的膝盖到脚腕裂开了一条大缝,小腿迎面骨被地上的碎石渣划破,串成线的血珠渗出来。
“您没事吧?”莎拉尽量放轻语气。看着被砸出个大凹陷的汽车和她勉强撑住的人,煞白的脸让她心悸,莎拉简短的询问让女人不好意思起来,游离的蓝眼珠扫视着莎拉,嘴里嚅喏着什么,她还没有从刚刚的惊魂一刻中缓过来,但习惯还是让她反复用着敬语感谢面前的救了她的人。
“米兰达!”一个矮小瘦弱的男人从大厦的旋转门出现,小跑着过来,手上拎的东西甩来甩去。盘发女人靠在路边的花坛,用手扶着太阳穴。莎拉给男人让出位子,两人用莎拉听不懂的语言咕哝了几句,也许是德语,也许是俄语,女人说话时在不停的大喘气,泪珠滚落进她的胸脯。莎拉环视在场的其他人,街道对面有些年轻男女在远远地观望,他们是从电影院正对着的咖啡厅出来的。街角一个穿着蓝色连衣裙的母亲拉着女儿走了,不让她的头转向这边,一个男人在电话亭里偷瞄被砸烂的铁皮盒子,对电话里说着什么。离莎拉最近的一个老妇人在胸口划十字,另外几个人神情严肃地看着车上的死者。
“女士!”男人开口叫莎拉,“感谢!万分感激,我们会记得您的善行,永远永远都不会忘,但我们要先走了,我的妻子状况不太好,你知道的,她被这桩事吓坏了。”男人托着盘发女人的一边胳膊,另一只手摘下帽子不停地向她点头微笑。他倒退几步,看了眼死者,然后戴上帽子,搀扶着妻子走到对面的车上,几个大学生打扮的年轻人在看他们,他扶她坐进车里,再小跑到车的另一边钻进去。
有些看热闹的人散去了,但又有新的人围上来想一探究竟。不远处的鹬鸟随着潮水般涌来又退去,人们却在受难的同类的附近停留,将车辆层层包围。
莎拉·马里诺选择与人群相反的方向,她挤了出去,头也不回地离开了帝国大厦。死去的男人她认识,甚至有很深的印象——对于威廉·道格拉斯的下场,她甚至觉得自己早有预料。
帝国大厦的坠楼惨案发生的前一天中午,汤米·安吉洛得知一直和罗素·皮埃罗不对付的司机卡洛住在霍尔布鲁克,和一个妓女姘居。他不关注帮派里有些人的情况,对于汤米·安吉洛,卡洛只不过是个油滑但又缺乏能力的男人。如今他从整件事情的但和恩尼奥·萨列里的态度推至这样的结果:卡洛要有难了。
佩佩餐厅门面的大玻璃无一幸存,焦黑的窗沿和餐厅内越发旺盛的火焰散发着木板浓烈的焦臭味和化纤纺织品燃烧的气味。恩尼奥·萨列里扶着烫手的门框走了出来,回头看了一眼已经成为炼狱的地方。他还没有完全从刺激中缓过来,也不顾的西西里人该有的文雅和绅士风度,抽出胸袋的高档白丝巾胡乱擦拭着脸上的黑色煤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