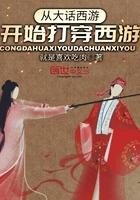秃鹫小说>祥瑞 王莽 > 第17章(第2页)
第17章(第2页)
《韩诗外传》记载了这个故事:
越裳氏重九译而至,献白雉于周公,曰:“道路悠远,山川幽深。恐使人之未达也,故重译而来。”周公曰:“吾何以见赐也?”译曰:“吾受命国之黄髪曰:‘久矣天之不迅风疾雨也,海之不波溢也,三年于兹矣。意者中国殆有圣人,盍往朝之。’于是来也。”周公乃敬求其所以来。1
这个故事极富诗意,又充满了喜庆色彩。
越裳氏经历了辗转翻译,给周公献上一只白雉。周公问,我有什么资格受你们的贡献呢?越裳氏通过翻译答道:“在我的国家里,连续三年风调雨顺,大海没有惊涛骇浪,老人说这是因为中原出了圣人,何不去朝贡一番呢。所以我们就来了。”
看,周公是辅佐幼主,今天的大司马王莽也是辅佐幼主;周公处理了“管蔡之乱”,稳定了周的政局,王莽也处理了董贤,稳定了汉的政局;周公的德行令越裳氏万里迢迢来献雉,王莽也是如此。而且周公那么大的功德,只得到了一只白雉,献给王莽的还多出两只黑雉,这岂不是超迈了周公的德泽?
《汉书》指出,越裳氏的位置不在益州的方向,所以这次献雉是王莽自导自演的闹剧。这极有可能,假如周公时期真的有一个越裳氏,过了一千年,还在同一个地方,还叫同一个名字,其概率微乎其微。
“一千年”很久,今人说起一千年前的宋朝,会觉得遥远得不得了。但对汉朝人来说,“一千年”只是越过秦返回周。孟子曾说“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周公之后五百年有孔子,孔子之后五百年有王莽,从周公至今正好是一千年2。
王莽把雉鸟献给了皇家宗庙,表示祥瑞要向汉朝的列祖列宗报告,而不是归功于自己。但群臣不难嗅出王莽与周公媲美的味道,当然,眼前这位外戚、权臣,似乎在儒学造诣上比汉朝以往的同类人物如田蚡、霍光等要高得多,人品也更高尚。这个祥瑞可能会令一些汉廷的官员感到诧异和震惊,但大多数官员会觉得这是锦上添花的好事。
5.汉家天下王氏安
王莽从一位失势的前任大司马,变成了堪比周公之德的帝国掌权者。这不能不说是上天的恩德。
雉鸟,便是上天恩德的明证。
面对这一祥瑞,群臣纷纷向王政君上奏王莽的功德,首次提出“安汉公”这个称号:
委任大司马莽定策定宗庙。故大司马霍光有安宗庙之功,益封三万户,畴其爵邑,比萧相国。莽宜如光故事。……莽功德致周成白雉之瑞,千载同符。圣王之法,臣有大功则生有美号,故周公及身在而托号于周。莽有定国安汉家之大功,宜赐号曰安汉公,益户,畴爵邑,上应古制,下准行事,以顺天心。3
“群臣”是史书原话。能称得上“群臣”,表明这是绝大多数官吏的意志。其中,有的官吏应出于对权臣的奉承,有的属于王莽势力,有的则对祥瑞深信不疑,有的是真心拥护。但不管怎样,“群臣”基本达成了共识,证明王莽的功德在时人看来符合事实:
第一,汉朝曾经有过大司马稳定政局、“安宗庙”的历史案例。当年霍光废昌邑王,立汉宣帝,开创汉朝中兴局面。王莽逐董贤、立箕子,功劳与霍光颉颃。既然霍光曾经比着汉代第一宰相萧何来封赏,那么王莽也应该如此。
第二,从儒家的“圣史”看,今天出现周公时期的祥瑞,说明王莽与周公同功同德。既然周公“托号于周”,那么王莽也可以托号于汉。
这两点理由,分别照应了“行事”——汉朝惯例,和“古制”——儒家制度,说明给王莽这一特殊的封赏——也就是“安汉公”的称号并非逾制。
“安汉公”,是一个非常奇特的称号,令人想起英国革命时克伦威尔被群下所上的尊号“LordProtector”。这个词被译为“护国公”,非常巧妙,与“安汉公”真是相得益彰。
多年之后,王莽在给朝廷的奏章里有一句自况:
臣莽伏自惟,爵为新都侯,号为安汉公,官为宰衡、太傅、大司马,爵贵、号尊、官重。4
王莽是把爵、号和官三者区分来看的。他成为安汉公的时候,爵位仍然是新都侯,这就说明安汉公不是爵位。他的官职当时还只是大司马,说明安汉公也不是官位。
安汉公是一个尊号,其特殊之处在于以国号为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