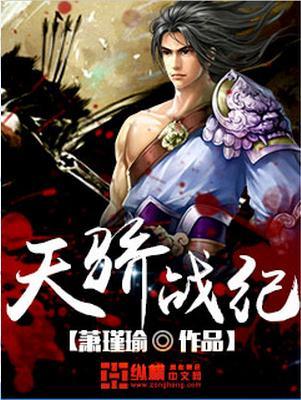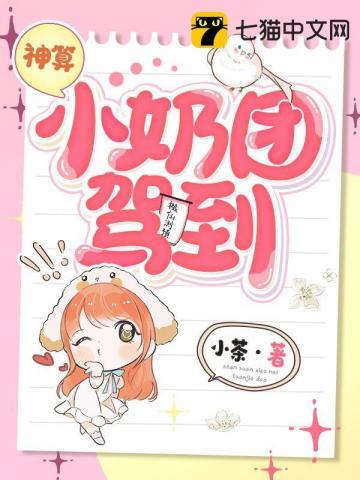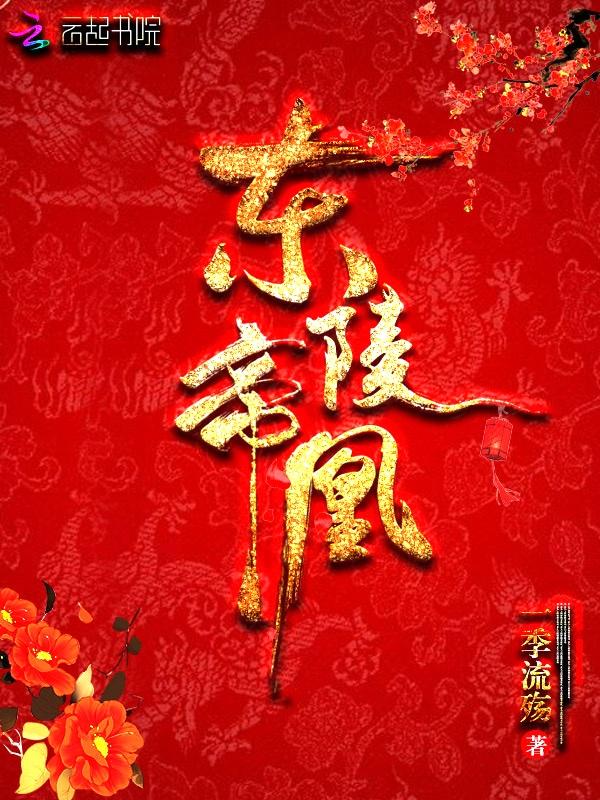秃鹫小说>祥瑞 王莽和他的时代 > 第55章(第2页)
第55章(第2页)
这一当就是九年,也是汉成帝越发奢侈荒淫、宠爱飞燕合德的九年。绥和二年(约公元前7年)的春天,发生了一次震惊内外的灾异。翟方进接到下属报告,说是天上出现了可怕的“荧惑守心”。荧惑,就是火星,是灾难之星;“心宿”则是天上的明堂,天子布政之所。荧惑守心,就是火星停留在“心宿”之内,意味着天子将有大灾难。
在《汉书》的记录里,秦始皇和汉高帝崩殂之前,都出现过荧惑守心的天象。
翟方进精通天文星历,知道“荧惑守心”的含义,不禁惊慌失措。消息传来,有人上书认为,要想消弭皇帝的灾祸,得选择大臣来厌胜。大臣的位置越高,效力就越强。翟方进知道自己的死期到了。
皇帝果然召见了他,所谈何事,后人不得而知。但他回来之后已经打算自杀,人还没死,皇帝的策书火速送到,措辞极为严厉,斥责他为相九年、灾异频出、未能称职。翟方进见策后自杀。
有汉以来,灾异影响政治并不鲜见,但像这样直接迫使丞相自杀还是第一次,足以说明此时的汉家天下,官民对灾异的信仰何等之深。但此事亦有颇多蹊跷之处:
一来,后世的天文学者推断出,这个月并没有发生“荧惑守心”!14实际发生的是“荧惑入太微”,这也是对天子不利的凶相。二来,翟方进精通星历,“荧惑守心”并不是流星那类刹那间消失的天象,能延续一两个月,他为什么没有辩白,而是很快自杀?三来,这一时期,王莽已经除掉淳于长,当上了大司马,而翟方进与淳于长关系密切,又是丞相,和担任大司马的王莽分庭抗礼。此事和王莽有无干系?四来,翟方进死后,皇帝却“祕之”,就是秘密、低调处理这件事,没有公开,但给了翟方进超规格的葬礼,多次亲自凭吊,这种待遇之高,以至于多年后翟方进的儿子翟义起兵反抗王莽时还念念不忘。
因此,这次所谓“荧惑守心”的灾异,很可能出于一次未经记录的宫廷政变。翟方进担任丞相时间太久,树敌又多,与王氏家族关系不佳,王莽新晋,两人成为政坛上的对手15。因此,翟方进的反对派们利用这次灾异,将其夸张或解读为最凶险的“荧惑守心”,推动汉成帝有了令丞相自杀以代自己的想法。汉成帝召见翟方进,可能是要求甚至恳求翟方进自杀,那封措辞严厉的策书,只不过是程序,并非真的斥责。所以汉成帝才会赐予高规格的葬礼,以表示由衷的谢意甚至歉意。这也可以解释,何以是翟方进的儿子翟义举起了反对王莽的大旗,以及王莽为何对翟氏家族斩草除根,连儿童也不放过。
但这更说明了,经学最为重要的武器——言说灾异,已经失去了驯服君主的初心和威力。汉朝人信鬼神、信天命,对灾异祥瑞很敏感,董仲舒才会在这基础上发明“天人感应”的说辞,试图用灾异祥瑞来规诫帝王。很长一段时间里,这套说辞是有作用的。汉宣帝满世界去找祥瑞,本身就是他敬畏天命的表现。
但经学的文本是敞开的,任何懂得经学的人,都可以依照自己的目的解说,“灵活”借助灾异为自己的利益服务。翟方进之死,说明灾异成了惩治大臣而非规诫帝王的利器。其实,早在翟方进之前已经不乏先例——儒者谷永依附王氏家族,当别人以灾异批评王氏家族时,他却说灾异来自汉成帝无辜的许皇后,致使许皇后被废。总之,到了元、成之际,灾异已经成了政治斗争的工具,经学的公信力颇为降低。
尽管丞相以生命“厌胜”天象,但几个月后,汉成帝还是晏驾了。
10.今古之争
刘歆,恰恰是翟方进的学生,他自幼跟随父亲刘向修习今文经学,对诸子、术数、诗赋、方技都很有兴趣,又是宗室,少年之时就有了些许名气。汉成帝召见他,原本要任他为中常侍留在身旁,但被大司马王凤否了,只好让他先去当黄门郎。
巧合的是,大概不到两年,二十四岁的王莽也被拜为黄门郎。
两个人年龄相仿16,一个是刘氏宗室,一个是王氏外戚,他们长达一生的友谊虽然隙末凶终,但此时都还年轻,一起共事当有志同道合之感,他们会谈论天下大事,诸如儒学怎么发展,汉家怎么改制,经学有何种弊端,怎么以儒学来说灾异17,国家有哪些问题,等等,和后世的“有志青年”应该没有什么两样。
他俩也会去找黄门待诏扬雄聊天,扬雄比他们大十多岁,从蜀郡来到长安,被时任大司马王音召在门下,又推荐在黄门待诏,从此入仕;所谓待诏,就是等待皇帝下诏给个正式的官做,一般情况下,短则数月,长不过几年,都能得到机会。可惜王音很快去世,扬雄又是一个毫无官瘾、不求上进的人,所以他一直待诏,已近十载18。
好在扬雄志不在此,他口吃,内向,不爱说话,对今文章句之学也没有兴趣,喜好博览群书,有机会就去天禄阁读书。刘歆也曾跟随父亲在天禄阁校书,彼此就熟悉了。
小兄弟桓谭也加入了。他是太乐令之子,若以今天比照,是个喜欢“玩音乐”的“官二代”,尤其热爱被儒家所诋毁的“淫乐”。他对当时主流的今文经学也不感冒,倒是愿意学习古文学。
扬雄和桓谭可能不太会深度参与刘歆和王莽关于“天下往何处去”之类的论辩,但在对经学的态度上,他们应该意见一致:
那就是关于今文经学和古文学的看法。
所谓今文经学,简单来说,因为儒经最初主要是口口相传,再加上战国的战乱、秦朝的《挟书令》,很多经书的简帛文本没有流传下来。直到汉朝,学者们才通过记忆默写下这些经书,他们使用的文字就是当时通用的文字,也就是“今文”,犹如今天人们使用简体字来抄写古代的书。
但是,那些先秦的旧书并没有也不可能彻底消失,有的被人保护着藏了起来,有的侥幸没有被销毁,例如汉景帝分封在曲阜的儿子鲁恭王在扩建宫殿的时候,偶然从孔子故居的墙壁里发现了一些儒经,都是用先秦的文字所写,于是大家称之为“古文”,犹如今天人们得到一本古书,上面印着繁体字。
因此,今文学、古文学最初只是文字或文献上的区别。当然,在人们默写、传播、抄录的过程中,儒经在文字、篇目、字数上会有不同,有些差别甚至还很关键,以至于后来“今文”和“古文”的内涵变成了截然不同的两个“学派”19。当然,此类问题到了后世才变得重要,在汉朝,刘歆和王莽的时代,真正重要的事情只有一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