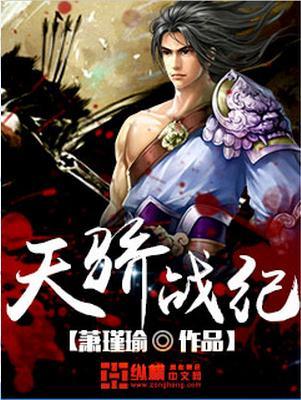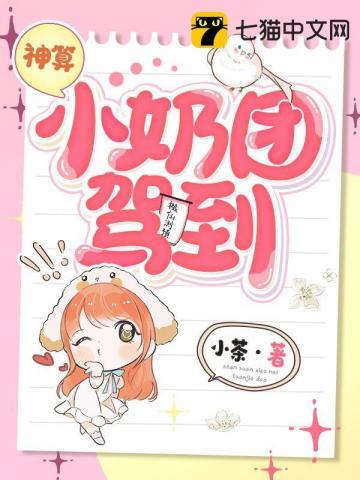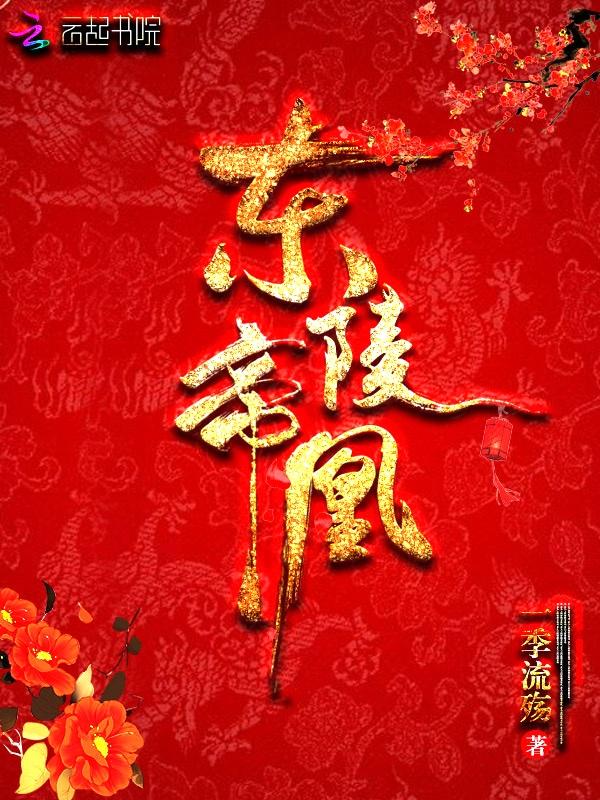秃鹫小说>祥瑞 王莽和他的时代 > 第55章(第1页)
第55章(第1页)
汉元帝即位才两年就杀了老师、辅臣、儒者萧望之,此事影响极大。
由儒学教导并被儒家寄予厚望的汉元帝,一度承载着儒家对圣君的期望。这种期望,包括重用儒臣,打击文法吏,消除社会问题,爱民爱人,制礼作乐,推动礼制改革,等等许多具体的内容。但是,汉元帝很快以阴柔之手段杀掉师傅,仅此一件事,就足以寒了广大儒生的心。换句话说,汉元帝就此失去了圣君的资格,儒家只能另选哲人王。后来的汉成帝、汉哀帝比汉元帝更不如。人们选择王莽,也包括了对汉帝的失望。
不过,汉元帝可能从一开始就没有想成为儒家的圣君。他的确笃信儒学,但毕竟也是汉宣帝的儿子,承袭的是汉宣帝留下的政治格局。以往,史家会特别强调汉宣帝“乱我家法者,太子也”的故事,但汉宣帝既然还是将帝位传给了他,那么一定会从多方面对儿子进行教导、传授、安排,尽可能消弭元帝的性格弱点。
既笃信儒学,宽容节俭,又遵循父教,信任文法宦官10,这种撕裂或许是汉元帝给后人留下“牵制文义,优游不断”11印象的原因。而儒学,也就在皇帝的这种优柔寡断中折向了新的方向。
9.翟方进之死
当然,从另一个角度看,萧望之的死是皇权尚未衰微、“汉道”仍然在发挥作用的表现。到了汉元帝的儿子汉成帝,“霸王道杂之”的格局渐渐不复存在,儒家终于如愿以偿地实现了“独尊儒术”,一系列礼乐制度改革在儒家推动下徐徐展开。
长安城无恙,未央宫无恙,但汉廷内外的气氛悄然改变。
表面来看,儒学已经接近胜利,十四家经学博士法度森严,牢固把控着帝国的意识形态;中央地方的高级官员几乎没有不是儒家出身的,丞相基本都是大儒,连外戚王氏家族也好儒养士;整个社会向着礼乐制度的终极理想前进,就等着圣人出来实现天下太平。
但经学的繁荣之下,隐藏着不可忽视的危机。
首先,那些官方的经学博士们日益僵化,他们一代传一代,老师传弟子,父亲传儿子,每一代都在前人的基础上对儒经做出更多、更新、更复杂的解释。几个字的“经”,会有“章句、传、记、说”等不同体裁的诠释,字数越来越多,有位叫作秦延君的经师,解释《尚书·尧典》,光“尧典”这个题目,就解了十万字;其中“曰若稽古”一句,解释到三万字。
多年以后,执政的王莽下令修订删减这些章句,博士弟子郭路在删减时,因为工作量太大,不幸累死在灯下。
文本的烦琐复杂,师法和家法的门户之见,使得今文经学日益成为小圈子里的文字游戏。纵然皇帝信任他们,即使俸禄不会减少,但他们对思想与学术的贡献已经不如从前,对后学者的吸引力也大打折扣。
但与此同时,今文经学作为博取名利、仕途升迁的通道却始终通畅。修习经学依然是儒生们趋之若鹜的康庄大道,于是被选拔出的儒臣,有许多儒学素质很高,道德水准却堪忧。
前文曾提到,汉成帝的丞相匡衡,父祖都是农夫,幼年“凿壁借光”勤奋读书,很是励志。他专精《诗经》,入仕之后当过经学博士、太子少傅,直至封为乐安侯,成为丞相。
匡衡不愧为《诗经》大师,流传后世的奏章处处以《诗经》为准则,告诫皇帝要遵守教化,维系道德,为民父母,不可耽溺情欲。这些道理当然是对的,但匡衡自己在面对石显等人的权势时,反而闭口不言。更奇葩的是,他所封的乐安侯国一开始边界不清,把临近郡的土地也划了进来。匡衡明知有错,但隐瞒贪占了这部分土地及其租税,直至被人告发,丢掉丞相大位,被免为庶人。
尽管如此,匡衡的许多子孙依然凭借经学家法,继续充任博士职位,逍遥于仕途。
匡衡之败是不够“谨慎”,安昌侯张禹就精明得多。张禹也是博士出身,专治《论语》,位至丞相。在张禹的时代,《论语》的地位虽然不如“五经”,但也渐渐重要起来,当时的《论语》有多个版本,张禹凭借自己出色的经学素养,对《论语》进行比勘修订,搞出一个定本,人称“张侯论”,风靡后世12,也就是今天《论语》的通行版本,而其他版本渐渐亡佚,张禹的水平可见一斑。
政治上,张禹却缺乏丞相的担当,不敢与外戚王凤争锋;私下里做生意、买田产,凭丞相之尊搞了不少泾河与渭河岸边的肥沃土地。他深居简出,庭院深深,喜欢一个人在院子深处鼓弄丝竹,尽享音乐之美。如此这般,比起匡衡的“晚节不保”,同样“腐朽堕落”的张禹反而得以善终。
匡衡、张禹都是当世大儒、学术领袖、一代经师,他们尚且如此,那些遍布朝廷和郡县的儒生官员就可想而知,社会并没有变得更好,今文经学的声誉和品质也就受到了损害。
当然,并非所有人都如此。
高陵侯翟方进也担任汉成帝的丞相,就颇能做到廉洁克己、赏罚分明。翟方进自幼失去父亲,少年时在汝南郡当小吏,备受太守摧折,一气之下来到长安学习儒学谋求上进,他的后母很疼爱他,跟着在长安“陪读”,给别人织鞋子挣钱供他读书。
多年以后,翟方进成了治《春秋》的大儒,当了博士,尤其精通《穀梁传》,还爱好《左传》,刘歆就在他门下学《左传》。
翟方进为人和盖宽饶相似,史书称他“持法刻深,举奏牧守九卿,峻文深诋,中伤者尤多”。13越是对高官,他越苛刻,深文周纳打击他们,奏免京兆尹、右扶风等二千石以上高官二十多位,政敌陈咸被他打击到忧愤而死。显然,这种做派得罪了不少官员,但赢得了舆论的赞赏和皇帝的信任,最终一路当上丞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