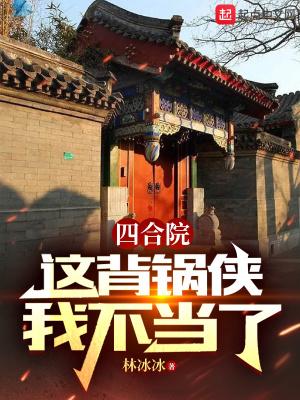秃鹫小说>云海沉浮 对句 > 阿常(第2页)
阿常(第2页)
那么活生生的一个人儿,成了一具躯壳,睡在膝盖高的土堆下边。
他找了块木板,一笔一画地写下母亲的碑文。
这也成了他一生中最后一次写作。
他没再打开那个装着未完成手稿的箱子,他干着零活,浑浑噩噩地度日子,还染上了烟瘾。他蹲在田间地头,和五大三粗的汉子们在一起喝得酩酊大醉,没人会觉得他读过书,也不会有人知道他曾是个秀才。只是那些男人们会笑着揶揄他,说他细胳膊细腿的,像个文人而不像苦工。他也只是抽烟,听水烟冒出咕噜咕噜的声音,偶尔回以一个沉默的笑,但再也没人关心这笑背后什么意思。
那天,他把那个装了书稿的箱子打开了,他拍拍书皮,轻轻吹去灰尘,看着它呆了好久。
“我看着他缠着白绫上吊的,那白绫还是从地主家那儿接的。”阿常低头抚着那个黑亮的烟斗。
“他自杀了?”我问。
“是啊,连遗书也没写。也许不知道写了该给谁看吧。”阿常低垂着眼眸,睫毛纤长,像一对扑闪的蝴蝶,“我当时没法儿救他,就算救了他,那又能怎样呢?”
周常山死了。书灵沉默许久,从书中出来,拾走了他的烟斗,也背上了书箱。
“他不算坏人,我带着他的烟斗去了衍江,也算替他看了吧。”
衍江距离那个山村很远。
在路上,阿常路过一个小山村,因为常年在外,书页有些已经损伤泛黄了,阿常决定在这儿休息一段时日,把那些残破的书页重新抄写一遍,好留存下来。
有个热心的木匠,见他书箱破旧,主动提出帮他修书箱,还让他在他家里住下了。听说阿常要抄书,他也提出要一块儿帮他抄。
“太麻烦你了,不必了。”阿常说。
“没关系!反正我这木匠生意也少。闲着也是闲着。”他很热情,阿常不好拒绝。
但阿常也不白住,每天去买菜回来,给匠人做饭。
时间一久了,村里人就打趣木匠:“你小子啥时候找到这么一个俊俏的戏子做媳妇?”
匠人红了耳根,说话含糊,却没有否认。
这些阿常都看在眼里,但他不做任何反应。
匠人从不让阿常洗菜洗碗。
“谢谢大哥。”阿常倚着门框看他洗碗,眼里带着笑意。
匠人盯着碗,脸却发烫:“姑娘不必多礼,你做饭,我洗碗,这是应当的。”
阿常张了张嘴,没有说话。
正因匠人以为阿常是女儿身,所以每次阿常谎称要去洗澡时,匠人都老实地呆在屋里。可书怎么会洗澡呢?阿常在山林里随意走了走,回去时看见匠人在给他抄书,但耳根红得像要滴血。
“姑娘,你这是什么书?”
“我大哥写的,他要我送到京城去。”
“……姑娘可曾看过书的内容?”
“不必看。”
一个月后,阿常发现他写字的速度明显变慢了,抄书的次数也少了。
像是在故意拖延时间。
于是那天,阿常说:“大哥,我这部分都抄完了,你那部分没抄完的话,分我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