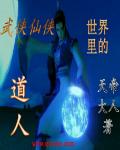秃鹫小说>大秦帝国献公 > 086章 郑当时的拖字诀(第1页)
086章 郑当时的拖字诀(第1页)
翌日,天光正好。
将闾并未大张旗鼓,只带了章邯与杜周二人,乘坐一辆不起眼的马车,来到了位于咸阳城南的治粟内史衙门。
衙门口的守卫显然得了吩咐,见到将闾下车走进来,他们并未阻拦,只是躬身行礼。
与丞相府、太尉府等显赫衙署相比,治粟内史衙门显得朴素许多,门脸不大。
治粟内史郑当时,领着几位主要的属官,早已等候在衙门正堂。
“下官郑当时,参见监国殿下。”郑当时年约五旬,面容清癯,穿着一身浆洗得有些发白的官服,态度倒是恭谨,一丝不苟地行了大礼。
他身后几位官员也跟着行礼,只是眼神中或多或少都带着些探究和疏离。
将闾虚扶了一下:“郑大人不必多礼,诸位请起。”
他目光平静地扫过眼前这些人。
郑当时,扶苏的坚定支持者之一,以迂腐固执闻名,能在掌管钱粮的要害位置上待这么久,显然不是个简单角色。
至于他身后的那几位,看样子都是衙门里的老人,眼神里透着一股子“我们自成体系”的默契。
这治粟内史衙门,怕是针插不进,水泼不进啊。
“本殿今日前来,是奉父皇之命,监管治粟内史事务。”将闾开门见山,并未多做寒暄,“衙门内的日常运作,依旧由郑大人主持。本殿只看大局,调配钱粮以应国用。”
郑当时躬身道:“殿下放心,下官等必当恪尽职守,全力配合殿下。”
这话说得倒是漂亮。
将闾点点头,也不急着查账簿,只是在郑当时的陪同下,象征性地巡视了一圈衙门各处。
库房、账房、官吏办公的处所……一切都显得井井有条,却又透着一股子陈旧刻板的气息,仿佛时间在这里都流淌得慢了几分。
杜周跟在后面,看着那些堆积如山的竹简和算筹,眼神有些发直。
他这搞格物的脑袋,实在对这些繁琐的文书账目提不起兴趣,只盼着殿下赶紧办完事,好回去继续琢磨他的新弩。
章邯则默不作声,锐利的目光不动声色地扫过每一个官员的脸,将他们的细微表情尽收眼底。
巡视完毕,众人回到正堂落座。
将闾也不绕弯子,直接道:“郑大人,本殿眼下有几项急务,需要衙门调拨钱粮支持。”
郑当时连忙正襟危坐:“殿下请讲,下官洗耳恭听。”
“其一,格物院新式军械已进入量产阶段,急需一批精铁及铜料,预算暂定为……五十万钱,另需粟米五万石,作为工匠口粮及耗用。”将闾报出一个数字。
“嘶……”郑当时身后,立刻响起几声压抑不住的抽气声。
五十万钱?
五万石粟米?
这手笔也太大了!
格物院那地方,他们早有耳闻,只当是九殿下弄出来的新奇玩意儿,没想到耗费竟如此惊人。
杜周忍不住挺了挺胸膛,格物院是他的心血,如今能得到如此大的投入,他与有荣焉。
将闾没理会那些小动作,继续道:“其二,关中水利工程需追加投入,以扩大修缮范围,确保来年灌溉无虞,预算……三十万钱。”
又是一个不小的数目。关中乃京畿之地,水利自然重要,但这追加的数目,也着实不少。
“其三,新式农具已在部分地区试用,效果显著。为鼓励农人使用,需拨付一笔款项,作为推广补贴,暂定……二十万钱。”
三项加起来,不多不少正好一百万钱,外加五万石粟米。
将闾说完,端起面前的茶水轻轻吹了吹,目光落在郑当时脸上。
郑当时脸上的肌肉抽动了几下,原本还算恭谨的表情,此刻变得有些为难,甚至带上了一丝愁苦。
他放下手中的茶盏,搓了搓手干咳两声:“殿下……这……这数目着实不小啊。”
将闾放下茶杯:“郑大人觉得,哪一项不该投入?”
“不不不,殿下误会了。”郑当时连忙摆手,“殿下所言三事,皆是利国利民的大好事,下官岂敢有异议?只是……只是……”
他面露难色,语气也变得吞吞吐吐:“只是这国库支用,向来有严格的规章制度。如此巨大的款项,按照《秦律》和内史府的规程,需先核实各处用项细目,再由各司主官会签,然后报少府复核,最后……最后还要上报丞相府备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