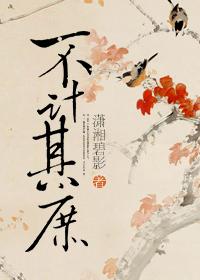秃鹫小说>大秦帝国献公 > 045章 树欲静而风不止(第2页)
045章 树欲静而风不止(第2页)
咸阳城内几家世代经营粮草、垄断农具生意的商号,敏锐地察觉到这小纸片背后潜藏的威胁。
官府直接参与农具推广,还发行了这种近乎货币的东西,这无疑是在动他们的蛋糕。
于是,市面上开始悄然流传起各种流言:
“那官府的纸片,就是糊弄人的玩意儿,指不定哪天就换不成粮食了!”
“听说监国公子要用这纸片子把大家的粮食都收走!”
甚至有人暗地里找到持有凭证的农户,用极低的价格收购,试图制造恐慌,扼杀这新生事物于萌芽。
“殿下,果然不出您所料,有人在背后捣鬼。”杜周收到消息,立刻向将闾汇报,言语间带着几分气愤。
将闾面色平静:“意料之中。新旧交替,总会触动既得利益者。按预案行事。”
杜周领命,立刻展开反击。一方面,他在各试点县的官府兑换点,堆出小山般的粮食和布匹,保证所有前来兑换的凭证(初期以小额为主)都能立刻兑付,用实打实的行动粉碎谣言,稳定人心。
另一方面,廷尉府的吏员悄然出动,顺藤摸瓜,迅速抓捕了几个散布谣言最凶、暗中低价收购凭证的典型人物,游街示众,杀鸡儆猴。
双管齐下,效果显著。凭证的信用得以稳固,暗流被暂时压制。
这段时间,长公子扶苏遵照嬴政的旨意,一直随行观察新政试点。亲眼目睹水车之利、曲辕犁之便,他由衷赞叹将闾的智慧与务实。
然而,当看到官府发行“凭证”,甚至动用吏员打击那些商贾时,他温厚的眉头再次蹙起。
一日,他找到将闾,私下里表达了自己的忧虑:“九弟,水车、新犁确是利民之举,为兄亦深感钦佩。然这‘官府凭证’,以官府信用代替钱帛,直接干预市易流通,更有打压商贾之嫌,此举……是否过于激进?恐有‘与民争利’之虞,失却商贾之心,非长久之道啊。”
将闾停下手中的笔,看向这位宅心仁厚的兄长,语气平和:“兄长所言之‘民’,是指何人?”
扶苏一愣:“自然是指天下万民,包括士农工商。”
“然也。”将闾点头,“但兄长可知,当下之利,被谁所占?是囤积居奇、操控物价的豪商大贾,还是那些辛勤耕作、却常年受盘剥的底层农工?”
他站起身,走到窗边,望着远处的田野:“我发行凭证,并非要与所有商贾为敌,而是要打破少数人对粮食、农具等基础物资的垄断,稳定物价,让利于最广大的农人、匠人。官府掌控部分流通,是为了防止奸商趁机盘剥百姓,是为了让新政的红利,真正落到实处。”
“短期内,或许会引起部分商贾不满,看似‘与民争利’,实则是与‘豪强争利’,而让利于庶民。此中阵痛是为了大秦更长远的稳固与繁荣。若一味纵容豪强兼并,贫富悬殊,纵有仁政,亦难长久。”
将闾的一番话,如同一道光,照亮了扶苏心中某些固有的认知盲区。
他开始重新思考“民”的定义,思考仁政与铁腕之间的平衡。虽然仍有疑虑,但他看向将闾的眼神,多了几分理解与深思。
他这个九弟对万事万物的理解,似乎总是与众不同。
试点区域的初步成果很快被汇总起来。杜周将详细的数据——灌溉效率提升了多少,耕作时间缩短了几何,农人对新工具和凭证的反馈,以及遇到的阻力与应对措施,全部整理成一份简洁明了的简报。
将闾亲自将这份简报呈送给嬴政。嬴政仔细翻阅,看到效率提升的数字时,满意地点点头。当看到关于官府凭证及其引发的风波时,他沉吟片刻,最终在简报上批复了八个字:“谨慎试之,观其后效。”
帝王的认可,无疑给新政注入了强心剂。
然而,树欲静而风不止。
就在试点工作有条不紊推进之际,咸阳城内几家最大的粮商,联合了数家与旧楚、旧魏贵族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大商号,突然集体行动。
他们并未直接对抗官府,而是选择了一条更“合规”的路径——联名向丞相李斯递交了一份措辞恳切、声泪俱下的陈情书。
书中历数官府凭证如何扰乱市场秩序,指责监国公子干预经济乃是“违背先贤古法”,痛陈此举将导致商路断绝,百业凋敝的可怕后果,恳请始皇帝陛下明察秋毫,废止此弊政,以安商贾之心,维系大秦经济命脉。
李斯拿着这份分量沉甸甸的陈情书,眉头紧锁。他知道,这不仅仅是几家商号的抱怨,其背后牵扯的势力盘根错节。
一场围绕着经济控制权,新政与旧规的激烈交锋,已然正式拉开了序幕。
咸阳城,刚刚平息的波澜,又将再起风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