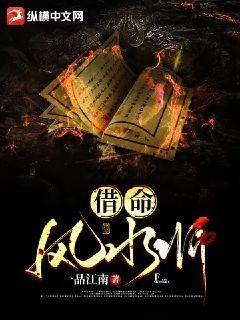秃鹫小说>大雪压青松青松挺且直全诗 > 第55章(第3页)
第55章(第3页)
他从山路一路向下,走不多时到了四喜堂。三姑娘正靠在门边百无聊赖地等,见他过来,便焦急地朝他挥手,催促道:
「阿凶,快些快些!你上哪儿去了——」
哥舒岚觉得自己的心脏仿佛变得越来越大,跳动的声音仿佛就在耳边。肺部翕张的空间变得愈发小,那颗心就快要从喉咙中跳出去了……
他仍是小跑几步。
「你再不来,那对双胞胎的娘亲就要把我二姐姐撕了……」谭妙真嘴上不饶人,急促地将他肩头竹筐取下,飞快地朝屋里跑去。
哥舒岚喘息着,艰难地看着她的背影越来越远……
「咚——」
……
再醒来,天色已经黑透了。
哥舒岚艰难地偏过头,刚一动弹便被又小又凉的一双手轻轻托住。谭衔霜声音轻柔,与照看她的那些年幼的患者时并无两样:
「做什么?别动。」
她的手就搁在哥舒岚烧毁了的半边脸上,他紫红可怖的伤疤被她摸在手里,却也和抚摸那些孩子光洁的脸颊一样。
哥舒岚烧毁的脸上有一双忧郁的眼睛,谭衔霜走到哪里,他的眼睛就跟到哪里。她倒一杯水回来,看他这样又轻轻笑起来:
「你这样看着我,我倒是不好意思了。」
谭衔霜虽这样说,可从她脸上却看不出一点羞赧之色,反倒让听这话的男人脸红了——若他的脸没被烧坏,那必定是红透了。
她将水喂给他,哥舒岚伤重的时候早被她喂过千百回了,可他依旧不能不理所应当而又心无旁骛地接受这一切。
兴许是他心里有鬼,这杯水喝得他胆战心惊。一晃神,他呛一口。
「怎么了?」谭衔霜问,可哥舒岚就在她面前丶在她手中,因为一口水咳出血来。
哥舒岚看着她手心里的黑血,连自己都吓了一跳。他惊愕地喘息,无助地抬头望着她。可谭衔霜神色平静,掏出手帕擦掉自己手心的血,又轻轻地擦拭他的嘴角。
「你中毒了,自己之前知道吗?」
哥舒岚诧异地摇头。
「我想也是……」谭衔霜将手帕丢在火盆里,不久便都烧成灰烬,「你中的毒名叫斥息,你知道那是什么吗?」
他又摇摇头。
谭衔霜凑近他,极认真而又轻柔说道:「是你身上那瓶翦水花唯一的解药。」
*
五色的蚕丝线卷在线轴上,乱而有序地丢再地上。那位相府里的高娘子如同一只化作人形的六眼蜘蛛,指尖的蚕丝犹如蛛丝,盘根错节,将落入其中的人尽数绞杀。
哥舒岚抱着刀站在一旁,等那高娘子将手中绣品完成——她向来是不将手中活计做完便不说话的。
哥舒岚手中的刀没有名字,只是随手拿来地一把劈柴的旧刀罢了。他的那把不知春给了他那当做女儿养的小徒弟,他自己那一身功力不是因拿了什么刀便会不同的。
高吟吟绣完那白玉郎君腰间的红色珠络,才终于抬起头,对身旁丫鬟道:
「云舒,看茶。」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