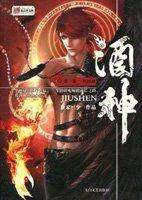秃鹫小说>他也跟着疯了四年叫什么名字 > 18第 18 章(第1页)
18第 18 章(第1页)
虽说紫舒证明了自己的身份,甚至暗卫从街坊邻居中打听的消息也不似曾经的云禧,但萧慎敬这个人疑心重。
再加上派去查询她底细的人还没消息回来,以防她偷偷逃跑,自然是不会彻底放任不管。
云禧走后不久,萧慎敬换了身低调的青衣,带着几个贴身侍卫来到了瘦西湖畔。
一望无际的桑田看得他直皱眉。
一旁的顾文谦徐徐说道:“桑田侵塘,遇雨则涝。太湖流域围湖造田种桑,导致泄洪能力下降太湖流域水患频增,而这大运河流域虽说还未曾如太湖流域一般,但桑田再如此扩充下去,怕也必然会导致如斯结果。”
萧慎敬没说话。
蹲下身,指尖捻着片枯黄的桑叶,衣摆沾满泥浆,一行暗卫正在百步外的茶棚警戒,马蹄声惊飞了桑树枝头啃食嫩芽的灰雀。
景全八年的界石歪在田埂旁,上面"永业田"的刻痕正被桑树根须一点点撑裂。
日头正盛,一老者跪在桑田里。露水浸透的粗麻短褐紧贴着脊背,他伸出三根手指捏住叶背的白色霉斑——这是今春第三回闹蚕病了。六岁的小女儿蹲在田埂上,正把泛着绿沫的沟渠水舀进木桶,水里漂着隔壁王寡妇昨夜悬梁用的半截麻绳。
他掐了片叶子问道“老丈,这叶子怎的泛了铁锈色?”
老农浑浊的眼珠转了转,突然扯着嗓子唱起扬州小调:“二月卖新丝,五月粜新谷。。。”
村落,土墙上墨迹未干的官府告示正在秋风里翻卷,露出"每户需缴生丝二十斤"的朱砂批注。
萧慎敬眉头猛地一皱。想起他在瓜洲渡看到的漕船,甲板上堆满的苏绣杭罗,此刻突然化作压在这些佝偻脊背上的巨石。
等老者背着蚕叶回去时,萧慎敬也跟了上去。
一路闲话,他越听神情越发莫测。
都说江浙一带富庶,可当老农颤巍巍掀开茅草屋角落的米缸,半缸霉变的陈米里蠕动的米虫,让萧慎敬想起奉天殿早朝时,户部尚书奏报的“江浙岁入生丝百万担”。
老者看着自家米缸底层的陶罐,“这里面埋着我大女儿被丝车绞断的食指……”
他的话还未说完,门外里长的铜锣又在催缴夏税。
老者抓起生锈的镰刀“真他娘的想砍了这些祸害人的桑树,却在冲向门口时颓然垂下“今秋若再缴不足丝税,砍桑的就会是拿着官契的税吏,可这一亩桑田产丝约五斤,才能卖一两六钱,而亩税就要九钱……一家子人可怎么活?”
萧慎敬回到客栈时天已经黑了。
他拿起密折在烛火下观看,范子石的奏折再次刺痛了年轻帝王的双目——
“今观湖州府岁贡生丝三百万两,而耕织小民竟至鬻儿卖女,此非天灾,实乃人祸。臣冒死以闻,伏乞陛下垂鉴……湖州府产出生丝价值约三百万两白银,国库仅收入四十七万两,地方官府截留八十三万两,商帮获利一百二十万两,而二十万蚕农仅得五十万两,人均不足二两五钱……官商勾结九重吸血,暗夺半数之利……样丝之毒:漕运之恶:印子钱狠:织造之贪……蚕妇缫丝,灯下千转方得一线;墨吏贪银,席间半盏即耗万钱。今湖丝岁贡可造四十万匹锦,若使蚕农得活,则东南可安,国库可实。若纵蠹虫啃噬,恐他日龙袍织就之日,即是饥民揭竿之时。”
重农抑商的改革势在必行。
萧慎敬一拍书案。
稻田改桑的确收益倍增,但逐年增加的桑田,早已动摇了国之根本。
如今扬州府桑田已占耕地的六成,粮价较景德时期涨了五倍有余。若遇天灾,粮食短缺,普罗大众如何能活?
而且那些欺上瞒下的贪官蛀石也得一一血洗干净。
萧慎敬又在书案后沉思了许久,直到婢女进来剪烛火时,他才站起身,走到窗户下,看着不远处高耸的钟楼,他突然开口“让刀一把今日的暗卫叫来。”
刀一略微思索就知道了萧慎敬说的是谁,赶紧把负责监看紫舒的暗卫叫了过来。
暗卫一进房间,立刻跪下回禀道:“今日那位紫舒小姐并没有任何出逃的行为。”
“她做了什么?”萧慎敬已经回到了书案边,拿起了吸饱墨汁的狼毫。
“中午和徐元思在房间用过膳,后来,两人又一起在后院葡萄藤下纳凉,紫舒姑娘睡着后徐元思将她抱了回去。”
萧慎敬写字的手顿了顿“抱回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