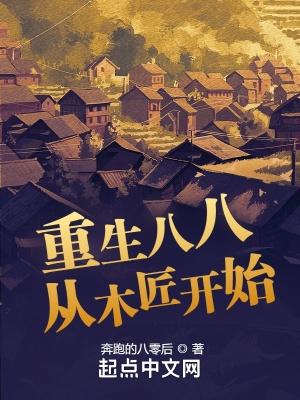秃鹫小说>心动后遗症意栀 > 第80章(第2页)
第80章(第2页)
她这一觉睡得很长,好像做了很多梦,梦醒那一刹那,她又把所有都忘干净了,脑袋昏沉沉。
手指抹过湿痕,她忽然想到了下午,
孟谨礼站在她跟前,修长的手指近在脸侧,看见她眼泪刹不住后,他微微弯着指节,准备拭过她的眼泪。
他离她很近,他的味道也是,熟悉的冷香中还有淡淡的药味,
软膏擦在他为救她受的伤上,甚至伤是她的滑雪板造成的。
擦药的棉签早就在慌乱中掉到了地上,她抬着眼眸望着他,他的神情总让她恍惚到从前,
还没有分开的时候,
她知道百依百顺久了会腻,她有时候会故意耍些小性子,这个时候,孟谨礼就会哄她,递来一个台阶,在温柔乡里,他们很快「和好」。
偶尔她会觉得,他把她当成了没有长大的小朋友,他现在说话的语气,和滑雪场哄小女孩的语气很像,甚至要更温柔。
她也不知道是怎么了,突然很委屈很委屈,尖刺刺不下去,柔软也不愿意轻易展开,根本没有准备好去面对所有。
前一刻还在想着如何拒绝划清关系,后一秒,就被人用婚约求婚了,
看上去很荒唐,
连戏剧也编不出来的荒唐。
她知道,自己不是一个豁达的人,
也是在那一刻,她正视到,那个被困在过去的人里,也有她。
想签字吗?
不知道,
都怪他,一下子把漂亮话都说尽了,让她费心费力在脑中拼命找漏洞。
然后,她看着他问:「孟谨礼,为什么是我?」
温热的手指拂过了泪珠,那寸肌肤立马泛起了酥酥麻麻的痒意。
他说……
忽然,走廊处传来了动静,
听上去像行李滚轮滑动的声音。
那道声音越来越近,越来越近,
停下来了,
在她房间的门口。
四下重新归于寂静。
他说过他要去参加妹妹的婚礼,要走四天,再回来也许是第三站。
此时此刻,他停在外面,她坐在里面,
一门之隔。
心跳快了几拍,她僵直着身子没有动。
她回房间的时候没有拿那份协议,当时孟谨礼正在抽纸,准备帮她擦眼泪。
她趁着这个空隙,吸了吸鼻子,逃跑似的望门口走,胡乱地擦了擦眼泪,留下了一句:「我先回去了。」
他有跟上来叫住她,
她的脚步却没有停,反而更快了,不似从前趾高气扬,是害怕到落荒而逃。
哭的时候最害怕别人哄,她更不希望自己再哭。
回到房间后,她浑浑噩噩也忘记打开灯,浑身没什么力气,胸口处闷闷的很难受,
什么也不想做,什么也不想想,她直接靠去了床边休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