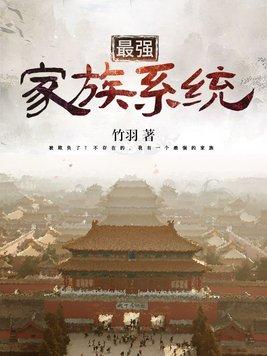秃鹫小说>咸鱼是什么字 > 第25章(第2页)
第25章(第2页)
贵暗施奸计,先生万不能于此刻直言!」
日光渐盛,透过斑驳的窗棂,洒在陈祭酒苍白的面庞上,他忽然笑道:「我明白了,你早已预见此间种种,刘臻向来是个耳根子软的,如今忽然反对新政,也是听了你的话,是不是?」
单孟闻言心头一惊,赶忙撩袍跪下,张了张口想要解释,最后却只道:「……学生罪该万死。」
满室寂静,窗外风声渐响,鸟声聒噪。
单孟跪了许久,才听上方叹息般传来一声:「罢了,你起来,不必跪我。」
他猛地抬起头。
陈祭酒看向窗外,咳了几声,说:「你向来是个聪明,有主见的。刘臻有你在身边,无论如何,他总不会吃亏。」
单孟轻声开口,「……先生?」
「你回去吧,也别再叫我先生。」
「不……先生,我……」
陈祭酒努力地撑起身体,站起身来,过了好久才叹出一口又悲又潮的气。
「单孟,也许你做的对。人各有志,我并不责怪你。」
「我虽寒门出身,却幸得机遇,步入仕途,这一路走来,深知民间疾苦,百姓不易。」他长叹一声,「若我,一个曾受风霜雪雨洗礼的寒门之子,都不再为他们抗争,那么这世间,还有谁会出声?」
单孟摇了摇头,「先生,您寒门入仕,竟能做到国子监祭酒之职。这其中权谋机变也好,学海渊长也罢,您历经波折,能在世家之间站稳脚跟,绝不是凭藉孤勇热血!」
陈祭酒低声笑了笑,道:「是啊,我从前便是这样,能躲就躲,什么都不敢做,什么也不敢说,徒劳死了许多人。」
单孟听他谈及往日秘辛,脑中「嗡」地一声,顿觉木已成舟,他张了张口,却被那人打断。
「我早已想好,无论如何我都会出头,你不必再说。」陈祭酒侧头盯着窗外的日光,慢慢道:「我只希望,莫要再连累你们。」
晌午时,仆人进来送药服侍祭酒午睡。单孟走出房门时还是恍惚的,他只觉得陈祭酒不该这么做。
这世间多的是厚此薄彼,畸轻畸重。若真想要改变,唯有筹谋心机,明哲保身。
站在世家之间为平民发声,实在是不自量力,以卵击石。
只不过是自我安慰的把戏罢了。
*
午后的蝉鸣已然不如前些日子激烈,叶帘堂身上的伤好了许多,现在已经不怕睡觉翻身了。只是右手的贯穿伤仍然时不时抽痛。
这日终于将目光幽怨,絮絮叨叨个不停的林太医送至马车上。
那边还在滔滔不绝:「叶大人,我前些日子才同你说要爱惜身体,你便,你便……真是气煞我也!」
叶帘堂吐了吐舌头,「太医,我也不想啊,谁都不想受伤啊。」
林太医目光倏地一沉,道:「我不过问你因何受伤,我只告诉你……右手,恐怕是要废了。」
叶帘堂愣了愣,轻声问:「好不了了吗?」
林太医叹一口气,摇了摇头,「大人,往后需得适应左手做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