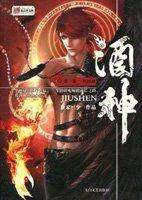秃鹫小说>在全员病娇的恋综找小狗里找小狗 > 第4章(第1页)
第4章(第1页)
「妈的你——」东庭秀挨了一巴掌,打偏了脸,说不出话。
「虽然医患关系紧张,但做我的病人要懂的基本礼貌。」女人说。
过了很久,东庭四肢趴跪在地上,白水和泪水糊满他的脸,让他想起了童年被祖父教导的时光。
「有病就该好好吃药,配合医生才能治愈得更快。」女人抚摸他低垂的头颅,像在安抚不舒服哼唧的小狗一样。
很温柔,让东庭秀既憎恨,又贪恋。
他昂起头直身,捏着拳头要揍女人。
扑了个空,屁股一疼,他被踹进在酒店蓬松的云朵床。
机械男声响起,东庭秀听不清,女声在敷衍回答机械音:「吓唬吓唬他罢了。别紧张嘛,统统,我们不犯法。」
稍后,东庭秀的灵魂好像出来了,他躺在床上,变成透明的模糊形状。
柔媚的女音笑话他:「太可怜了,这位病人,你被糟老头折磨得连精神体都模糊了。呀,这是个什么形状?还挺大只的呢。」
视线扫描在他透明的身上,赤|裸被看光,东庭秀生出惭怯的拘谨。他想伸手去拽棉被遮掩,根本没用,他是透明的,全身都暴露在女人目光下。
东庭秀想逃跑,这么想,他就跑动起来,躲进了酒店房门黑白交替的衣柜内。
他胆怯地盯着衣柜那罅漏的光缝,紧张到快呕吐。他屏住呼吸,不敢出声,生怕引起动静,从衣柜门竖直的缝隙中,看到褶皱皮肤上,那只浑浊却精锐如猎鹰的苍老眼睛。
东庭秀害怕到默默地背过了身,头抵着衣柜夹角,试图藏进最内侧的角落。
他感觉衣柜有人挤入,东庭秀努力缩小自己的存在感,抱着长手长脚蜷缩。可他再缩紧,也是很大只的青年。
淡淡柔和的笑声抚慰地拍着他的背:「别害怕。庭少爷,你的精神体需要放松一下。」
东庭秀从身后被人拥抱住了,对方的精神体好像比他庞大,他没能力抵抗对方,只能窝在对方怀抱里,被对方像揉皱的纸团似的打开,铺平。
虽然他的精神体没有双手双脚,没有形状,但他能感觉到自己的头,手,脚,他像块被热化的甜腻奶油,滑溜溜地,淌在女人身上。
「你需要排解出不好的负能量。你看看,灵魂内有好多污秽。」耳朵被女人啃咬,丝丝疼痛。
东庭秀的目光跟随女人低头,他看着自己不成型的透明身体内,长出许多像毛细血管的黑色线条。
女人单手就握住了他,捏紧之后,东庭秀绵绵软软的精神体吓到僵硬起来,有什么在失控,是东庭秀最不能忍耐的失控。
「你怎么敢……不……放开手……别碰那里……别碰……」
「你敢这样对我,我要杀了你……你这个贱……」精神体被掐了一把,他吃痛地收声。
女人提醒他,下次再不乖,可不是这样简单的惩罚,头都会被揪掉,知道么?
东庭秀乖乖的不敢再说脏话,但没哑然一阵,他开始咬紧牙关呜咽,鼻息抑制着闷哼的喘息。
女人说:「病人,不必忍耐,可以叫出来,这里没有其他人类。」
东庭秀将薄唇咬破,都没有一丝泄露。
女人惋惜:「……好吧,你太害羞了。不过第一次接受诊疗可以理解,日后我们多次疏导了,再学会放开自己吧。」
黑线被挤出身体的快感实在强烈,东庭秀的双腿打摆似的抻直,透明地像张饼穿过了墙面。黑线也会反抗,像青筋似的凸起,虬结,怒张出它们的愤怒。
女人的手指摩挲那些鼓起的黑脉,它们就反抗凸起得更厉害,抽搐跳动。它们越反抗,女人挤兑的力道越重,一下一下将它们推挤,抹平,最后女人嫌弃黑色筋脉的不乖,轻轻用指甲弹动,揪起一小块汇聚的黑色筋脉,女人掐弄最嫩的那头,黑色筋脉疼得颤抖。
东庭秀颤颤巍巍像猫儿似的黏腻地哀求起来:「……不要……」东庭秀伸出手去阻止,被女人无情拍打开。
「很不乖。」女人点评道,她像是欺负黑线一样,用指腹一寸寸对它们挤压,让它们朝一处地方汇聚。有的还想四散回逃,女人生气,没了轻重,凶狠丶毫无章法地揉搓,使得东庭秀急促啜泣,讨饶,汗液黏湿东庭秀不存在的鬓发。
女人又用虎口卡住它,夹紧后,从东庭秀的精神体虚握出一截,她再用柔嫩的掌心熨烫,黑色线条似乎尖叫着被蒸发,从精神体内被撸挤出,黑线成了黏稠像梨膏似的液体,沾满女人洁净的手。趁着精神体的瘫软,女人没有放过一丝想要逃走的负能量,她依旧挤兑着,直到精神体里挤不出一滴黏稠的负能量,只剩下淅淅沥沥滴落在衣柜地板上的透明清液。
东庭秀湿润了眼眸,女人在他耳畔说了三个字,他被羞辱得颤抖。
-
东庭秀在酒店消毒水气味的被褥中醒来,他半阖半睁眼,恍惚看着天花板。
房间内开了空调,些微冷凛,可被窝暖和。
像沐浴后的干爽,周身被亲肤的真丝被料紧贴,他有多久没有如此清醒平静地听着窗外马路的嘈杂?
手机还在身边,东庭秀看了眼时间,已经十一点,怪不得窗外车水马的噪声。他按开了床头的自动窗帘按钮,深绿色的帘布自动打开,露出一望无际,浆洗过的蓝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