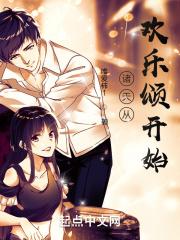秃鹫小说>天才帝师他不解风情免费阅读 > 16功成身退(第1页)
16功成身退(第1页)
“幕后之人终于现身了。”
萧憬好整以暇盯着韩易之的脸,却未从其上瞧见一丝一毫慌乱。
韩易之勾起唇角,“陛下果然聪慧。”
这话听着有些大逆不道,可放在韩易之口中,倒也不算什么。他是齐王的老师,当年可是与陈谕修针锋相对,各为自己的学生角逐帝位的帝师之选。
齐王败了,败给了他那个曾遭人白眼、耻笑市井的胞兄。而韩易之也似乎成了败者的老师,在朝堂上辅佐他人的学生。
他瞧着萧憬,恍惚时会想起萧悦。
“韩侍郎精心筹谋此局,究竟有什么深意呢?”萧憬翘起二郎腿,舒适地靠在椅背上,斜视着韩易之。
他总是这样自得,且在闲适过头的韩易之面前,须更加坦然松弛,才能不显得紧绷和违和。
“没有深意,臣是鬼迷心窍,有违圣人之德。”
韩易之颔首,说起这话却脸不红心不跳,丝毫未见其愧对圣人的心绪。
萧憬哼哼一笑,窗棂子外的阳光恰好打在脸上,他伸手去挡,在脸上投下一片阴影。他眼神转了个弯儿,一扬下巴抬向眼前摆满了奏本的书案,“这些走科举上来的文臣,说起圣人之德来便一套又一套,殊不知私德不修,将几位圣人的仁义道德随着官场上迎来送往的陋习一同吃进了肚子。”
可又话锋一转,“韩侍郎,你并非这样的人。你是辅佐齐王角逐皇位之人,应当懂得官场上犹如无形战场,刀枪无眼,明争暗斗,岂是区区一句圣人之德便可以搪塞过去的?”
说白了,萧憬不信他的鬼话。
韩易之此人,虽无功无过,可早些年也是很有些抱负的。说起来,他不比陈谕修差在哪里,肚子里有墨水,官场上懂进退,只是时运不济,总不遂心愿罢了。
听罢这些言语,韩易之出神了良久。他眼神落在萧憬书案前的一摞又一摞奏本上,思绪飘向了久远的过往。
他何曾想过,自己的心绪被萧憬点破,心中怅然,好似有波涛涌起,久久不能平静。
韩易之在京城没有朋友,却可笑只能勉强认萧憬为知音。
他摇着头笑起来,竟然在萧憬面前,踱步到窗前。他任由刺眼的光芒照在自己脸上,暖意便也席卷全身。
“大堇有了陛下和偃卿,无忧了。”韩易之突兀道。
萧憬身上的阳光陡然被他夺走,本还有些不悦,眨眼间,却见到韩易之眼角有些濡湿,似乎是掉了眼泪。
他瞪大了眼睛,屏气不语。
“臣有一个不情之请,”韩易之揩去眼角泪痕,语气渐有了波澜,“望陛下为臣照看好妻子儿女,臣便将兵部之职从此卸下,不论下狱或是赐死,不要牵连臣的家人。”
听这话,萧憬皱眉,有些生气,“在韩侍郎心中,朕会因此事牵连到你的家人?”
韩易之摇了摇头,“非陛下,也有旁人。”
萧憬脑中一转,“朕可以答应你,但是你要如实告诉朕,为何要苦心孤诣设下此局?”
自那日陈祥在金銮殿弹劾赵德安起,仅仅过了三日,却暗中翻涌起无数细小的波涛,在不经意间将局势推向顶峰。
有人要借刀杀人。
这把刀,便正是左佥都御史杨晃。他当日远在宿凉督察棉税,分不开身,顾不上京城陡然生变,便营造了杨晃逼迫陈祥弹劾上疏,于暗处与王党的孙贯撕破脸的假象,实则他在此事上着实无辜。待将此事捅开来,赵德安的罪过便已经定下了,不得不查上一番。
此时谁是那把刀,已经不重要了,此时真正要紧的是,这把刀究竟捅向了谁?
“臣已落法网,实在没什么好说的了。”韩易之缄口不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