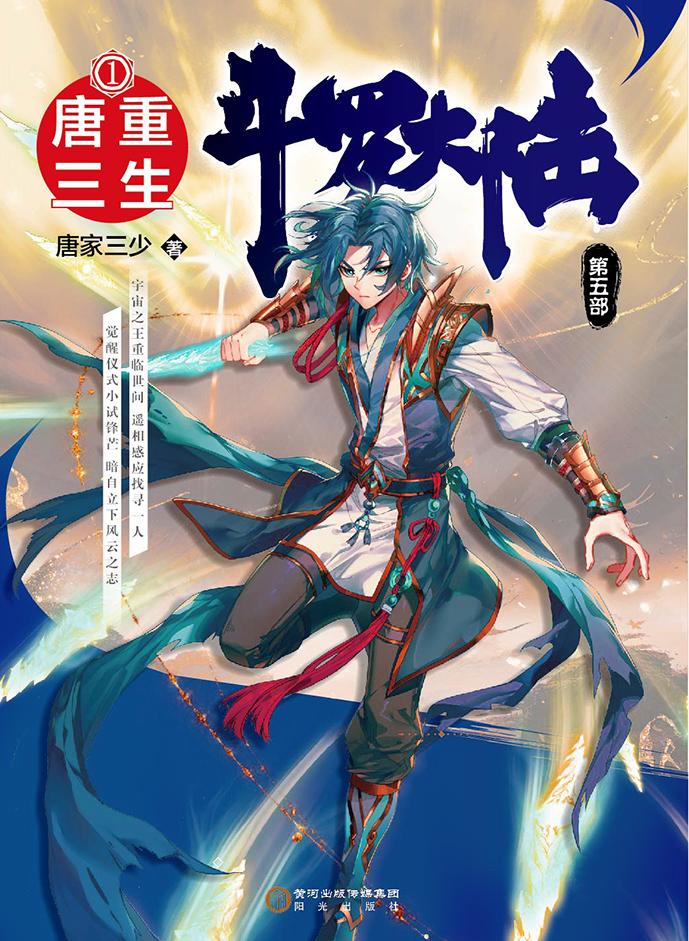秃鹫小说>戏精夫妇今天掉马了吗 > 煤山 但愿苍生俱饱暖(第1页)
煤山 但愿苍生俱饱暖(第1页)
“郎君在说什么,果然是我菌羹吃多了,还以为是二哥在讨封,郎君,是否想问二哥是谁?”宋惜霜捏着绣帕揉揉眼睛,换了一副迷瞪不清的模样。
“我祖母养了只鹦哥叫八郎,它去岁生了四只蛋,我们按其破壳先后便管它叫大哥,二哥……”
宋惜霜眼如弯月,她眼见面前郎君笑而不语,食指勾着那白玉菩提甩来甩去,后背沁出了一层汗。
“十一娘谢过郎君方才的称赞,只是我见识浅薄,今日第一次见到郎君,还不知贵府主君与宋家何旧?”宋惜霜攥紧了贴于小腹前的双手,镇定道。
她既圆了谎,便不该再如此被动下去。
何况,宋惜霜笃定,这人身份比她的窘境更难宣之于口。
东方昼单手背于身后,左手旋转的红痣蓦地静了下来,白玉菩提子溜过那颗蛊人的红痣,滑过苍白的指尖与腕间的青筋脉络,像条白蛇直钻如袖中消失了。
“我与府上瑞熙堂老夫人有旧,倒是宋姑娘真的是……第一回见我么?”东方昼低声笑了,看向宋惜霜腹前广袖,仿佛看穿了她紧张不安的动作。
“我却觉得宋姑娘,似曾相识。”
东方昼移近两步,探出左手欲触上宋惜霜的眉眼。
就在这一息间,宋惜霜心中千回百转,顿时有了主意。
她“啪”一声打落对方苍白筠瘦的手,面上是憋足了气的绯红:“郎君竟如此无礼!胆敢出言不逊,哼,我要告诉祖母去,这是什么道理!”
宋惜霜装作被轻薄后气势冲冲寻宋老太君告状的样子,她提着厚重的广袖礼裙旋身就走,见背后那人不再出声后,脚步愈发迅捷。
她心如火焚,暗忖道:要命了,卜筮的怎么就没算到今日会碰上这讨命债的。
站在原地的东方昼见宋惜霜落荒而逃,嘴角轻轻一撇,似笑非笑。
“殿下,我去杀了她!”
从假山后骤然传出一道狠厉沙哑的女子嗓音。
孔雀蓝裙角飞扬,款款走出一位容貌秾艳,青眉吊眼的高俏女郎,她绾着南芮国随处可见的随云髻,髻上也入乡随俗佩着两支玉步摇,额前却挂着小辫与金坠,耳珠垂下蛇形流苏。
“梦蛟,我们这回来雍州,可不是为了捏死一只蚂蚁。”
东方昼扬起左臂,制止住了梦蛟跃跃欲试的动作,凝声道:“煤山的那群宵小,可都处理干净了?”
“殿下……恕奴无用,”梦蛟看着他手心的珠串停止了盘动,顺间慌了神,“严岿死了。”
东方昼嗤笑一声道:“还是那个人做的吗?”
梦蛟跪地不语,她额角淋漓,想到在煤山死得惨无人道的头目严岿,与四年前在流放途中的巡抚使瘟猪樊广死法列同,不由心神一颤。
樊广是在泥雨山崩解手时消失不见的,他被玄翎卫发现时已四肢俱断,被十七根木桩钉死在一位老妓的床榻上,口中还含着他生前珍爱的贼驴东西。
此后经年,东方昼私巡稽案,在民间无私公正的“眀寰太子”的形象愈加深刻,但凡因盘根错节的官场庇人,便会被那“侠士”报复。
而雍州煤山山主严岿,向来以清廉刚直的品性被煤山上下敬仰。
“严岿大人,于三日前被监矿吏在新矿中找到其尸,亦是如樊广四肢俱断,被木桩钉在壁上,且口含那块凤髓石,只是……”梦蛟跪地,头垂得更低了,“当时人群喧杂,那块凤髓已不见踪迹了。”
据说是上巳时,煤山的一个稚子运煤时溜入煤洞,刨到块遗失千年的凤髓石。
梦蛟视死如归,闭上了眼睛,却感到发髻一重,她伸手摸了摸,却磕到东方昼那只冰凉的指节,自己像被热油烫到般迅速缩回手。
她眼前的郎君双眸凉薄,青雘色袖子擦过她的面颊,雪松潮香飘至鼻尖。
“阿蛟,你为什么怕我?”东方昼将梦蛟发髻上的金簪插得更紧了,他熟练地扯出一个笑,“并不是每一个南芮的女郎都戴步摇,金筒簪比步摇更适合你。”
“殿下……我。”梦蛟面容“噌”一下红了。
东方昼却于袖中摩挲着指尖,好像沾上了什么不干净的东西。
他笑着看梦蛟跪在玉池边照水作镜,心中却想着方才对他满口谎话不脸红的姑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