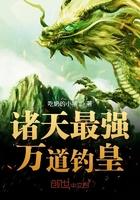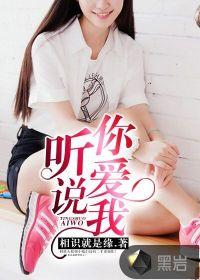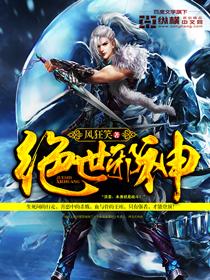秃鹫小说>你和朝阳一起存在作者是谁 > 翠湖老徐(第1页)
翠湖老徐(第1页)
丽江之行结束,两人飞到昆明,老徐会在明天到昆明办事。陈铭生准备带着杨昭在昆明转一转,顺便等老徐过来,然后见一面。
在昆明,陈铭生带着杨昭住在了他非常熟悉的翠湖宾馆,放好东西,他们到翠湖边转一转。十一月的翠湖,湖边上已经有很多从西伯利亚飞来过冬的红嘴鸥。
远远地,杨昭看到湖面波光粼粼,红嘴鸥在蓝天与碧水间肆意翱翔。它们身姿矫健,洁白的羽毛在阳光的照耀下闪烁着柔和的光芒。湖边上,有不少游客和遛娃的老人,三三两两的在喂红嘴鸥。
陈铭生侧过头问杨昭,“想喂吗?”
“嗯。”
陈铭生掏出钱包,从小贩的车子上,买了三袋红嘴鸥饲料。
饲料递到杨昭手中,牛皮纸的方形小袋子,陈铭生把袋子撕开一角,将饲料倒在手掌,对着湖面微微张开,低空掠过的红嘴鸥便停在了他的掌心。
陈铭生带着笑意的眼睛看向杨昭,“试试看,它们很温柔的。”
杨昭也学着陈铭生样子,喂红嘴鸥。
远处,红嘴鸥们在空中盘旋,舒展着修长的翅膀,优雅地划过天际,发出清脆悦耳的鸣叫,声音回荡在翠湖上空。杨昭看着它们轻盈地落在水面上,时而低头觅食,时而仰起头,灵动的眼睛好奇地张望着周围的人群,丝毫不怕生。
“陈铭生,你说大家喂红嘴鸥为什么不把饲料扔水里,都是拿着喂?”
“这其实,跟一个海鸥老人的故事有关……”
杨昭的目光似有期待,“你跟我说一说。”
陈铭生停下喂海鸥,趴在湖边的栏杆上,跟杨昭认真地说:“海鸥老人本名叫吴庆恒,他是一名普通的退休工人,在更久以前,他曾是西南联大的学生。他之前受过高等教育,思想激进,在特殊年代受了不少迫害,之后他就避免与人交流,自己过着孤独的日子。80年代的时候红嘴鸥第一次到昆明以后,他就找到了朋友,老人每天都会走20公里路从城郊到翠湖来喂海鸥,为了省钱,他舍不得坐5毛钱的公交车。就是这样节俭的老人,却把省下每一分钱都拿来买饼干、面包或者做鸡蛋饼干喂海鸥。他一辈子都孤孤单单的,直到他死后,人们才发现他最值钱的财产是给海鸥做鸡蛋饼干的6个鸡蛋,一袋面粉,这些,他自己都舍不得吃。”
听着陈铭生的故事,杨昭觉得震撼又感动。
陈铭生接着说:“据说,现在喂红嘴鸥时把鸥粮放在手里的方法就是他第一个采用的。因为老人觉得把食物丢到水里喂海鸥会污染食物和水源,导致红嘴鸥生病,他真的一辈子都把红嘴鸥当朋友。老人去世后,有好心人在翠湖为老人举行追悼会,海鸥们在老人的遗照前盘旋着,久久不愿离开。”
杨昭的目光中带着动容,“所以动物,其实也很通人性。”
“嗯。”陈铭生点点头,“翠湖边上,还有老人的雕像,你想去看看吗?”
杨昭点头,陈铭生笑了,他拉着杨昭的手,慢慢地往雕像的方向走。
路上,杨昭问,“陈铭生,你说之前你回昆明执行任务,也是住在翠湖宾馆。”
“嗯。”
“那你会经常到湖边上转转吗?”
“会啊。”
杨昭并不开口,她拉着陈铭生的手,静静地走在湖边,听他诉说着之前那些彼此错过的往事。
陈铭生淡淡一笑,“我来湖边上,没有喂红嘴鸥的心情。那时候,任务出了点麻烦,烟实在是抽的太多了,就来湖边上转转,故事也是听小学生说的。”
“你那时候,压力是挺大的。“
陈铭生接着说:“也有时候,出来不是因为压力。”
“因为什么?”
“想你。”陈铭生转过头,看着杨昭,“真的想,越想控制越控制不住。那年,也是冬天,翠湖边上的红嘴鸥也是这样成群结队,我在湖边上走,才发现:原来,自然也可以治愈人”
不知不觉间,他们走到海鸥老人的雕像边。杨昭看到海鸥老人的身形清瘦,脸上的皱纹如沟壑纵横。老人微微前倾的身子,仿佛正急切地走向他那群特殊的朋友——红嘴鸥。他的双手自然地伸向前方,微微弯曲,仿佛正捧着一把把鸥粮,准备撒向空中。
在雕像的边缘,他们把最后的鸥粮捧在手掌中,成群的红嘴鸥吸引到老人的身边。蓦地,一只红嘴鸥淘气地把鸟屎拉在了陈铭生夹克衫的肩膀上,陈铭生皱着眉头,眼神中带着嫌弃,“杨昭,你有纸吗?”
接过餐巾纸,一阵猛擦,夹克衫上还是留下了鸟屎的痕迹。陈铭生脸上似有愠色,“你看看你们,我喂你们吃鸥粮,你们还在我身上拉粑粑。
杨昭看到,忍不住笑,“没事,回去洗洗就掉了。”
“杨昭,我不干净了……”
沿着湖边向前,两人走着走着就看到了一座寺庙。山门前,熙攘的都市喧嚣瞬间被隔绝。抬头望去,那朱红色的山门庄严肃穆,飞檐斗拱如振翅欲飞的鹏鸟,在岁月的洗礼下依旧气势恢宏。门额上“圆通禅寺”四个大字苍劲有力。
杨昭似有惊喜,“这里还有寺庙吗?”
“嗯,圆通寺,昆明人说,这里很灵验。想去拜拜吗?”
“嗯。”杨昭点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