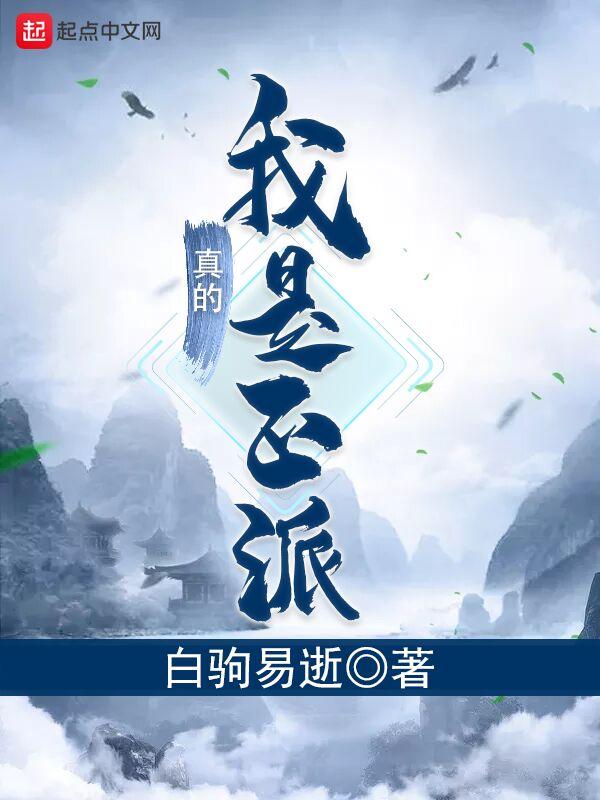秃鹫小说>清穿红楼大清富贵闲人十弋 > 120130(第6页)
120130(第6页)
平儿将炖好的燕窝粥递给王熙凤:“这是我亲自挑毛炖好的燕窝粥,奶奶高低吃两口。”
等到王熙凤拿着勺子舀了两口粥,再吃不下地放下碗,平儿才苦口婆心地劝道:“奶奶是什么身份,那些娼。妇又是什么台面上的人物,奶奶和她们置气,平白抬了他们的身份,左右有了大事,二爷能依仗的,也只有您一个而已。”
平儿果然最知王熙凤的心,被她这么一劝,王熙凤心头火热,她的风寒好似瞬间就好了,连忙吩咐平儿将管家婆子叫来,一扫病容,精神奕奕地安排起来。
没多久,贾家上下便都听闻了这个消息,三春整日在园子里住着,也是无聊,听了这事,暗暗挑拣起衣裳来,就连李纨,都少了层苦相。
若说谁不高兴,或许只有被贾政忽略了的王夫人,但这宴席的名目是为老太太尽孝,史老夫人都乐呵呵地等着,更兼之接下此事的也是她的侄女,便也只能咬牙忍了下来,还得小意奉承着老太太。
荣国府里上上下下都忙碌起来,至于如何开库房,如何陈设,又如何取摆件,多不多言,总之,在几番准备后,定在三月初三这日,这既是春景正盛之时,又是女儿家的节日,在这春光里,荣国府将开赏春宴。
黛玉接到的,就是这个宴会的帖子。
自从黛玉被赐婚后,请她的帖子一日比一日多,但黛玉对此只觉兴味索然,那一堆堆送来的帖子,十张里甚至都挑不出一张想去的,全部都以要在家闭门待嫁为理由拒绝。
但荣国府并不能如此对待,荣国府是黛玉的母舅家,贾家郑重的送来的帖子,黛玉若随意拒了,反倒显得她无礼。
在听了贾家嬷嬷所言,此宴会是为了让老太太赏春而办,黛玉就更没有理由拒绝了。
黛玉笑着接了贾府的帖子,好吃好喝地伺候了这两位嬷嬷一餐,等到雪雁好声好气地送走了那俩嬷嬷,回了院子后,黛玉也琢磨出了不对,摊开信纸,取过羊毫小笔,写下了一封信。
春日的日头并不刺眼,从打开的窗户中透了进来,将黛玉笼罩在其中,黛玉头上的头发丝被阳光照着,恍若细碎的浮金。
雪雁一时看得呆了,被黛玉用卷起的信封轻轻敲着额头,才回过神来,羞赧地笑着。
黛玉噗嗤笑了:“还是小时候那呆头呆脑的模样,这信找人给五阿哥送过去,若他有了回信,赶紧给我送来。”
雪雁也不把黛玉的调笑放在心上,她笑着应了声,便拿着信走了出去。
留下黛玉在书房里,往香炉里扔上一团香,又用海外的玫瑰胰子擦过手,在玉泉山的山泉水中洗净,将挂在壁上的古琴拿下,拿着尺谱弹起琴来。
乐声泠泠,古拙而典雅,就连园子里的鹤,听了这声音,也扑棱着翅膀,飞了过来,闻琴起舞。
南三所里,自从康熙动了让胤祺去当差的心思后,在南书房里的功课终于停了,再也不用起早贪黑,披星戴月地去读书。
当然,等到他正经入了朝,也得一大早起身,去乾清宫上早朝,只不过,他现在到底去哪儿,康熙还没有想好,还在观察、博弈阶段,他便也过了段轻松的日子,既不用早朝,也不用办事,更不要读书。
总之就是没有人管着的状态,每日里不过就是向皇太后与宜妃请安,然后便回南三所的屋子躺着,有兴致了拿着腰牌便能出宫,宫外的新鲜玩意儿也有人送进来。
这样的日子,简直比神仙还要舒服。
四阿哥胤禛已经去了工部当差,听闻他做事最为认真,已经得了康熙好几次夸奖,这让大阿哥和三阿哥内心更加焦灼,与这两人不同,胤祺对于胤禛的表现毫不关心,这样悠闲的日子,他恨不得能再多多的过上几日。
奈何,总有人看不得他这么清闲。
这不,当胤祺有一日躺在窗旁的榻上,将手中的杂谈随意盖在脸上,被太阳晒得昏昏欲睡之时,小太监蹑手蹑脚地走了进来。
“怎么了?”胤祺含糊着发声询问。
正垫着脚观察胤祺是否睡着的小太监,被吓得一跳,立时便将手中拿着的信递了上去:“五阿哥,林家姑娘的信。”
胤祺一早就吩咐过,黛玉送来的东西,必须第一时间递给他,这也是为何瞧着他在休息,小太监还敢打扰的原因。
紫檀嵌螺玳的炕桌上随意地放着些杂谈游记,胤祺将信放到那一摞书上面,唤着小太监要来热水,洁手净面,将瞌睡赶走后,再用绸缎将手擦干,胤祺这才将信撕开。
柔软的宣纸上字不多,内容却让胤祺冷笑连连。
贾政总以为他是聪明人,然而真正的聪明人又如何会在员外郎的位置上蹉跎这么多年。凭着他国公府少爷的出身,但凡真有本事,早就不是现在这个模样。
贾政的心思,浅得简直胤祺一眼就能看出。黛玉一时没有想到,也不过是不知道朝堂上的那场闹剧。
这么大张旗鼓地行事,也不怕犯了康熙的忌讳。
胤祺看着黛玉信中的贾府,只觉着他们在自取灭亡。
也不知太子如何就收了这么愚蠢的人家投靠。不过仔细想想,太子是名正言顺的储君,向他投诚的人又何止一家两户。
太子只要冷眼看着,有人给了他想要的,便提拔一二,若有人不慎犯了忌讳,那也与太子无关,更不会让他有半点损失。
想到这,胤祺直接将笔拿来,就着黛玉的信,匆匆写下回信,将纸平摊着晾干之时,只见被和煦春光照着,上头的墨迹慢慢干了,只剩:“你随性行事即可”几个自上,犹有湿润的墨痕。
等到信上的墨痕干透后,胤祺将纸叠好,令人立时给黛玉送去,太阳未下山之时,黛玉刚收了古琴,便收到了胤祺送来的信。
等展开信看完,黛玉这才恍然,为何贾府突然闹出这么大的阵仗,真是富贵险中求,这种风口浪尖的时候,其他人都恨不得缩着,贾府却跳了出来,也不怕康熙一怒之下,将荣国府给夺爵了。
只能说,是贾家的子孙实在过于不争气,没法子,只能想出这般剑走偏锋的法子,豁出去谋一场荣华。
很快,日子便到了三月三这一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