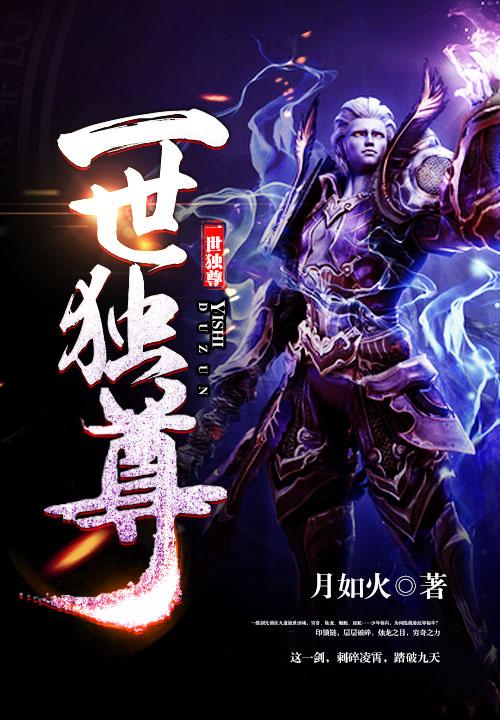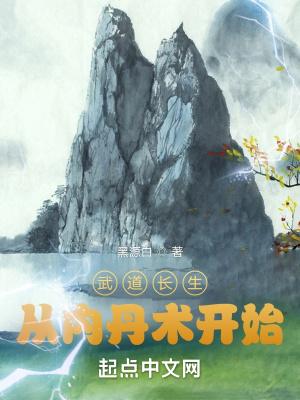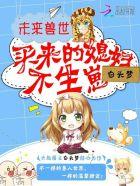秃鹫小说>darkelf曼陀罗花在哪 > 第18章(第1页)
第18章(第1页)
彭冬冬听得有些心虚,赶紧加重语气,带着点讨好的口吻说道:“我保证,我发誓!我一定回家吃饭!发洪水我也划船回去!”
电话那头传来一声轻笑,贾琳被他逗乐了,虽然语气依然带着点不满,但终究还是软了下来:“行了,别光说得好听,到时候让我和咱妈空等,我要你好看!”
她话锋一转,又问:“你喜欢吃什么菜?晚上我做。”
“都行,你做什么我都爱吃。”
贾琳随便哈拉了两句后,挂了电话。
那一头电话断了,但彭冬冬还握着手机,没有立刻放下,心里一阵酸涩涌上来。
记者的工作,意味着长时间的奔波和危险的采访,还有常人难以理解的精神压力。这份职业的坚持,无法用金钱衡量,但是对于彭冬冬来说,这不再是一份职业,更是一种使命,有着强烈的责任感和职业精神,才是支撑他一路走下去的动力。
彭冬冬的工资其实并不比贾琳高,但是伴随着隐藏的危险,这点他自己也清楚,曾经在见贾琳的父母时,岳父就明确表示因为这个原因反对他们结婚。老人的理由很直接——记者是个高危职业,说不定哪天人就挂了,他不希望自己的女儿有守寡的风险。彭冬冬当时站在客厅里,满脸尴尬,却只能硬着头皮听着这些不留情面的拒绝。后来,还是贾琳和她姐姐一起,好说歹说劝服了父亲。
即便如此,在婚礼当天,岳父端起酒杯敬酒时,还是意味深长地叮嘱了一句:“冬子,这个世界上,无论发生了什么,我的女儿永远要放在第一位。”
这句话,岳父说得郑重而缓慢,像是一份遗言,也像是一份重托。
彭冬冬连连点头,发誓会好好照顾贾琳。可多年过去,岳父的话却成了他心头的一根刺。他始终没有做到这句承诺,反而一次次因为工作忽略了家庭。
岳父去世后,这句话像一道烙印,深深刻在彭冬冬的心里。每次想到,都会让他感到一种无声的愧疚。他曾试图和贾琳解释,说自己来世一定会加倍偿还她和孩子所有的亏欠,但贾琳却总是笑着打趣他:“冬子,如果你是比诺曹,那鼻子现在都能通到天上去了!”
虽是句玩笑话,却戳中了彭冬冬的内心。
这些年来,他见过太多家庭矛盾,参与过无数次与家庭有关的采访和调解案例,他为别人排忧解难,却偏偏无法调解自己的家庭问题。
他常常对自己说:“家家有本难念的经。”
这句话听起来是安慰,却更像是逃避。工作与家庭的平衡,他一直没能学会。每次他因为一篇报导或一个新闻获得的荣誉,总会在心里对自己说:“值得!”
但这种自我安慰往往在看到贾琳和孩子失落的目光时被打破,让他清楚地意识到:无论职业多么崇高,家庭的缺席总是无法弥补的遗憾。但他又安慰自己,谁的日子不是缝缝补补又熬了三年再三年的呢?再难,也得继续走下去。
所以,今天,他下定决心,无论工作多忙也要按时回家吃饭。
这一次,他不仅按时离开了办公室,还特地绕路去了水果店,买了贾琳最爱吃的葡萄和石榴,算是一份带着歉意的赔礼。
拎着果篮的他,走在路上的脚步都显得比平时轻快了几分。(未完待续)
第18章
他要杀了我
【前言】在温情与危机交织的时刻,人与人之间的冲突与理解不断碰撞,揭示出人性深处的脆弱与坚韧。善与恶的较量不仅关乎选择,更是对责任与底线的考验。面对爱与的渴望,每一次抉择都如同夜色中的微光,虽微弱却能穿透黑暗,映照出生活的真谛:家是归属,责任是担当,而救赎,则是人与人之间不变的期许与希望。
打开家门,熟悉的饭菜香扑面而来。
客厅的灯光柔和而明亮,餐桌上已经摆满了菜,红烧肉的酱香,清炒时蔬的清新,还有一大锅热气腾腾的汤。厨房里隐隐传来贾琳忙碌的声音,一片温馨的景象。
他刚换上拖鞋,便听到母亲的声音从餐厅传来:“儿子,回来了,快换衣服,吃饭。”
母亲的声音温暖而亲切,一如他从记事起就听惯了的那种叫唤。
彭冬冬一时有些愣住了。他望向母亲,看着她从餐厅探出的身影,鬓角已经斑白,脸上刻着岁月的痕迹,可那双眼睛依旧明亮,透着慈爱与欣慰。
这简单的一句话,却让彭冬冬心头一热。小时候,每次他放学回家,母亲总是这样站在门口,喊他换衣服吃饭。那声音是属于家的声音,是他记忆里最深的温暖。如今他已经人到中年,走过了许多风风雨雨,但这份来自母亲的关怀依旧如初,丝毫未变。
他轻声说道:“诶,我这就来!妈,给您买了猕猴桃,新鲜的呢!”
“别破费了,妈不吃,留给自己吃吧。要不,留给儿媳妇吃。”
彭冬冬轻轻笑了笑,将果篮放在餐桌上,目光从母亲移向厨房的方向,正好看到贾琳端着最后一道菜走了出来。
他扬了扬眉,冲着母亲说道:“妈,猕猴桃是特地买给您的,吃吧!至于您儿媳妇,我可不敢怠慢她,我也给她买了葡萄和石榴,不然啊,小时候是您提我的耳朵,现在可是她提我的耳朵了。”
“妈老了,提不动你的耳朵了,当然只能由你媳妇来教育你了。你呀,就该多听听贾琳的,她这几年不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