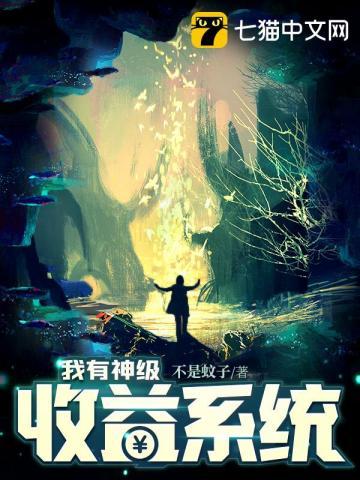秃鹫小说>替嫁王夫全文免费阅读 > 琵琶泣血(第2页)
琵琶泣血(第2页)
一句话刻薄地成煦说不出话,只能留在原地,看着她掀了毡帘离开。
“殿下!”
钱公公一声惊呼。
成煦强撑着的脊背脱力般倒了下去,胸口的月白长衫鲜红一片,隐约遏制不住。
阮阮回到清波院时,李徽容正在院子里浇花。
快入冬了,院子里不知何时移种了几株黄色腊梅,眼下虽尚未开花,红墙下枝干横斜也自有风趣。
李徽容放下水瓢,道:“太后娘娘千秋节将至,江大人递了折子贺寿,陛下已经准了他进京,不出十日就该到了。”
久违的好消息。
郁结数月的愁肠,总算多了一点点的寄托。
“看来今晚能睡个长觉了,”眉眼略略舒展,嘴角带了几分笑。
“你受伤了?”李徽容瞧见她衣袖上的一点血迹。
阮阮顺着她的视线看去,衣袖上沾了几缕血痕,大概是方才挣扎间沾到的。
略略开怀的情绪随着眼皮耷拉了下去,“不是我的,是他的。”
思及方才钱公公的话,“李姑娘,再麻烦你一次,殿下又受伤…”
阮阮还未说完,李徽容就把话接了过去,“我本就是行医问道之人,何况殿下身上还担着江南百万民众的生计,无谓麻烦之言。”
这话蹊跷,如今陛下亲政,除了西北军务外,一应奏本都是直送平章台,成煦和江南又有什么干系?
待要再问,李徽容已提了药箱,出门去了。阮阮也并未放在心上,拿起木桶里的水瓢,安安静静地给园中花草浇水。
这边安静祥和,坤宁宫寝殿里,却是山雨欲来之态。
近日帝后关系有所缓和,听闻一向勤勉的陛下今日竟有闲情去听戏,她一番盛装后打算意外相遇,没成想,陛下竟是为了那个女人。
明明她才是从正门乾清门抬进来的皇后国母,论才情、样貌、家世,哪一样比不过她,何以陛下如此厚此薄彼。
脑海中不断浮现长廊上两人携手相视的模样,她甚至在怀疑,那些情热难耐之时,陛下唤着的到底是“鸾鸾”,还是“阮阮”。
一旦疑心起,平地起波澜。
恰逢此时,陛下一道禁足的圣旨送到了坤宁宫,并将那个通风报信的小太监在众目睽睽之下活生生杖毙。
皇后娘娘花容失色,起身接旨时竟从宝座上直愣愣摔了下来。
皇帝体恤皇后身体欠安,将一应后宫事物都交给了两位贵妃。
昔日热闹的坤宁宫变成了如冷宫般的存在,风光无限的皇后娘娘终日只能坐在轮椅之上,心绪犹比深秋更为凄凉、幽怨。
冷清的坤宁宫外往东行去的寿康宫,却是日日欢声笑语、歌舞彻夜未停。
太后娘娘的今年的千秋节,是陛下亲政后第一次为母后筹办,自然比往年更为隆重。
阮阮早前收了太后娘娘的厚礼,既然人还在宫中,自然要备一份礼。
另外,哥哥已经入京。
一个出不去,一个进不来,至今未曾见面。
听闻太后千秋节,重臣勋贵都能入寿康宫贺寿,她正好借这个机会见一见哥哥。
只是如今身份尴尬,她要以什么名义去贺寿?
“殿下的仪仗到了,”李徽容正从东暖阁看诊回来,“殿下伤重去不了,请你替他给太后贺个寿。”
“这么多日,他没见好吗?”
阮阮思及他当日面色青灰,胸口的鲜血,心里有些不舒服。
李徽容未有言语,神色一如既往地淡,放下医箱,便收拣她在晒的甘草、黄芪去了。
成王殿下重病,卧床不起,连李神医都束手无策,这如今在宫里已经不是秘密。
宫里朝堂的风向总是变得很快,陛下愈来愈大权在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