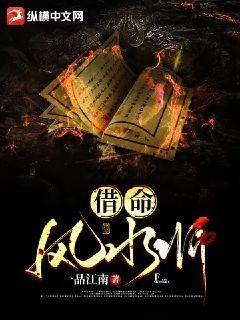秃鹫小说>hpfalsehood西里斯 > 第9章(第1页)
第9章(第1页)
一颗石子将阿普切绊倒,身前推着的大箱子应声倒地,那些包裹从推车口掉出来,砸在阿普切的胳膊和腿上,有点疼……手心,那枚金色的加隆依旧闪耀,尽管它浸染了点点血迹。“开一间房子,一直到八月三十一日。”抬头,阿普切将英镑堆在前台,倔强的看着那探究的看着自己的人。“你的父母呢?孩子,你不应该一个人出来的。”那脸上有些细细的小伤痕,身上略显古怪的袍子上也灰扑扑的,让这个精致的男孩有点狼狈,那个推车里的东西又多,杂乱的堆在一起“你的家在哪?我可以帮你叫一辆出租车的。”“他们在隔壁的酒店,因为没有空房间了我才到的这里,我不想打扰他们。”阿普切说,尽管那话有些含糊,甚至带着点点的哭腔,但是还好,他全力控制着自己。交涉了一会,或许太晚了,前台也不想耽误太久还是给他开了一个房间,并且叮嘱一定要将门关好,特快或许是因为太累,又或许是因为睡得太晚,阿普切这一觉直接睡到了下午,从床上坐起来,阿普切看着从窗帘缝隙里透出的阳光,拿着那个装着英镑的布口袋走出了酒店,他依旧穿着那身在周围人眼中有些奇怪的袍子,抵着头跟着前面的大人一起走出了酒店,幸亏前台换了人,阿普切才不至于被追问什么。站在街上,阿普切紧紧的攥着手中的布口袋,甚至想就这么跑回酒店,但是他没有,深深的呼吸着,就像平时自己在马戏团表演之前一样走进了一家服装店。他虽然有些缺乏常识,但是也知道不能太狼狈的去学校,他需要一件可以称得上是衣服的服装来蔽体,而不是那个灰突突的白色袍子。傍晚,当阿普切再次回到酒店的时候整个人变了一个样。白色的衬衫,黑色的外套,金色的扣子扣到了脖颈,这显得这个小孩有点不符合年纪的成熟,但是却更像教堂里的那些严谨的基督徒一样,黑色的长裤,一双黑色的皮鞋,手上还拎着对他来说有些重的购物袋。坐在床上,阿普切小心的将那些东西连同在对角巷买来的一起整整齐齐的放在行李箱里。扁扁嘴,阿普切想着那天自己在对角巷曾经看到过的巫师的样子,自己特意选了看起来和他们有点像的黑色衣裤,虽然这被服装店的人不认同。时间过的飞快,除了第一天,剩下的时间,阿普切几乎将自己整个人都扎在了峰区国家公园,他怀抱着那些奢望去寻找,累了就吃一块从酒店买来的三明治,坐下来看一会书。祈求着会在这里看到自己的家人,但是没有。那张羽毛上的地址就像在嘲笑着自己的愚蠢一样。八月三十一日下午,他退了酒店的房间,坐上火车前往伦敦。他不像别人可以拜托父母帮忙送到国王十字车站,所以只能自己提前一些,再提前一些。九月一日凌晨,他在路人的帮忙下找到了车站,小心的推着皮箱在那些站台中穿梭,旁边的人很少,阿普切来的很早,早到几乎是跟着车站开门一起走进来的,零星的几个人坐在车站的长椅上吃着自己的早餐,他们大多要赶第一班车。手中紧紧捏着那张车票,淡淡的汗水几乎要将整张车票晕湿,阿普切细细的数着站台上标记的数字,从一到九。看不到任何的不对劲,阿普切看着那个似乎就是第九和第十站台中间的墙壁。试探的伸出手摸了摸,瞬间睁大了双眼。那只手,仿佛穿透了一层透明的障碍然后穿到了墙壁里面。或许,这就是那个墙壁。阿普切想,小心的看着周围的人,再趁着别人不注意,猛地冲进了墙壁。再次睁眼,眼前是一辆红色的,看起来像一个蒸汽式火车一样的列车,头上的站台标记写着九又四分之三,阿普切对照了一下手中的车票,但是却没有看到检票的人,他看了看周围,现在还太早,天刚刚蒙蒙亮,距离麦格说的发车时间还有大概三四个小时的时间,所以基本没有人在车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