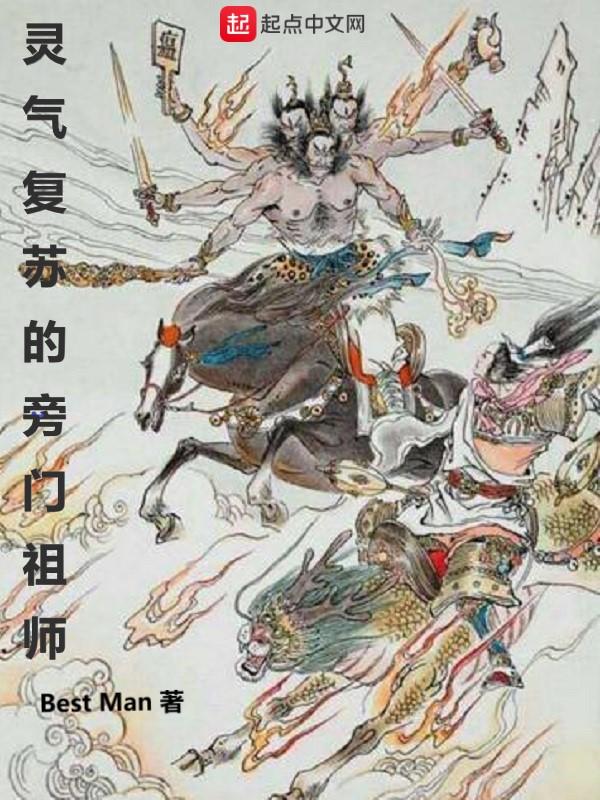秃鹫小说>偏宠一人笔趣阁 > 第6章(第1页)
第6章(第1页)
……种种打探来的消息,倒是让她心里稍定。若凭借自己实在难以达成所愿,她想,新帝在身为大皇子时曾去西南赈灾过一段时间,和范将军关系尚可,应当会为她提供一些帮助。虽然她要的不是帝王的一缕优待和同情,而是希望能借他人之手,揪出那个隐藏在这些黑暗真相后面的人。那位新帝,她曾见过一面,是一位冷峻深沉气势带有压迫感的男子,在他面前她总觉得压抑,如非必要,范青瑜并不想直接面见他。她低咳了几声,被大火熏燎过的嗓子到如今仍旧偶尔不适,除了粗哑之外,似乎也阻碍了她进食,以至于近日来越发消瘦。“小姐,药好了。”碧珠端着一碗熬得漆黑的汤药小心地过来,这是他们从荆州医馆拿的药,虽然久未见效,碧珠却觉得喝了总比看着自家小姐干熬难受强。范青瑜端过来,试了下温度,便一饮而尽。药汁辛辣,那张娇艳的脸上却未露出半分不适,放下碗,她便望着碧珠轻声道:“明日,我们便拿着那画像去找探子。”在两人躲进地道之前,范青瑜远远地将那纵火领头人的样子看的分明,虽然她画艺不精,但却也记住了那人的外貌特点,并铭记在心。虽然亲手将父亲下葬后,她们范府的主人便只剩下了养兄与她,可那些悉心打理将军府多年的人都是无辜的,还有祠堂里范家众先烈的立牌也在大火中付之一炬了。养兄……范青瑜想到对方仍在与乱党兵戈相见,心下便倏地一紧,玉白纤细的手有些颓然地撑在了桌上。兄长范青屹,是早年范大将军从流民中收养的孩子,范青瑜从来都是把他当做亲兄长看待的。范家以战功立足,范青瑜一介女儿身,又无其他本事,如今偌大一个将军府,只剩下他一人撑着了。她不辞而别,范青屹定然是生气的。她现在只希望那送出去的几封信哪怕有一封到他手里也好,不要让他再为自己担心了。“小姐,我们待会便去拜访江御医吧。”碧珠收起那药碗,眸中泛着一丝光亮地看着她,带着浓浓的期待。范青瑜看着这样的碧珠,微微弯起了嘴角,缓声答应了,“好。”江老御医的住处刚好离她们投宿的客栈不远,范青瑜换了一身淡色的长裙,戴着帷帽,和碧珠一起问路寻过去。在马车上待了这么多天,她们更宁愿自己靠脚走走,才有脚踩土地的真实感,更何况也能亲眼看看盛京。盛京的繁华,是她们从未见过的。路上喧闹的各色摊贩,鳞次栉比的精美楼阁,花红柳绿的各式招牌,人声鼎沸处的杂耍艺人说书人,一切都是那样鲜活热闹。一点都看不出不久以前,逆党作乱时人人自危街巷几近无人的萧条。范青瑜微微抬眼,透过帷帽看着眼前的这些从前想象过无数次的景象,却没有了以往在想象时的雀跃。范府众人此生都再也看不到这番盛景了。陪她从小到大的乳母走了,慈祥和蔼的管家阿伯走了,总是笑嘻嘻的小厮大河走了……和范府列祖列宗的牌位一起,都没了。这些人,命运和范家千丝万缕地联系在了一起,但他们却又是一个个无辜的人。她相信养兄一定会将西南平定,为父亲报仇,那些乱党也定会被剿灭,但恐怕除了她与养兄,还有这些人的家眷之外,无人会记得这些枉死的人。西南都府珲州城里,那些交好的人家,恐怕也不能理解她的这一丝执念,所以她也从未和他们说起。为什么凭借那虚无缥缈的三言两语就认定背后一定有这么个人呢?万一这其中有诈呢?再者,就算确实有人借机想要将范府一网打尽,她一个弱女子,独自来盛京又有何用呢?也许是,她不敢再面对那伤痕累累的家。“走吧。”范青瑜垂眸不再看,带着还在探头探脑的碧珠往江家所在的新月巷走去。没走多远,前路被人挡住了。几位锦衣华服公子模样的人嬉笑着走过来,领头的蓝袍少年上下打量着她,“哪里来的小娘子,大白天的还戴着帷帽,里面莫不是藏着一个绝世佳人?”虽说盛京的贵女们也会戴面纱和帷帽,但她们出行,哪一个不是前呼后拥,乘着华美车马的,眼前的小娘子,分明不像是那些大户人家的千金,那他们也不怕得罪什么人了。更何况,他们只是调笑几句罢了。范青瑜眸底波澜未动,带着碧珠低头行了一礼,粗哑的声音平静道:“小女貌丑,不敢惊扰公子。”一听见这枯哑粗糙的嗓音,几位少年纷纷面色一变,互相看了一眼,没趣地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