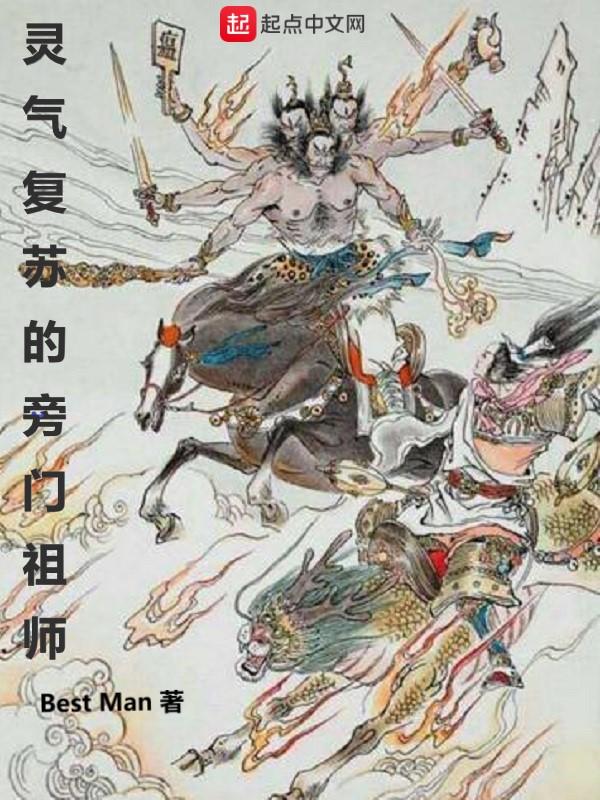秃鹫小说>度春风歌词 > 第94章(第1页)
第94章(第1页)
看了会儿窗外的景色,忍不住回过头道:“你当初……到底是为的什么,才去了雁门郡?”
这个疑问已经盘桓在他心中许久,今日又听孟皇后提起,困惑之意更甚,刚好正主坐在他旁边,能问个清楚明白。
梁承骁一撩眼皮,没问他怎么忽然提起这个,随意答道:“有很多方面原因吧。”
“孤年幼时,曾经历过一场刺杀,险些当场死去,运气好才捡回半条命。”
“皇帝查出了幕后主使,但将此事压下了,命任何人都不得声张。”他讥讽地笑了笑,“到现在他也没跟孟家交代清楚,刺客到底是谁派来的,不过想来就是那么几个人。”
“那是母后第一次跟皇帝翻脸,等孤的伤势好全,她就让舅父把孤带去了雁门——多亏了孟家势大,皇帝就算不愿意,碍于外头传的风言风语,也不得不点这个头。”
“……”
谢南枝虽然料到此事背后还有隐情,却不想竟是这样的缘由,一时有些愕然。
虎毒尚且不食子,晋帝竟然昏庸到了这个地步,纵容外人戕害自己的亲子,实在心狠手毒、罔顾人伦。
当年的事毕竟已经过去太久,连梁承骁自己都懒得放在心上,转过头时见谢南枝蹙着眉,神色含着几分自己都未曾察觉的愠怒,起初的意外和熨帖后,逐渐生出了一丝逗弄对方的心思。
“现在看来,母后的决定还是有远见。”他假作叹气说,“要是孤从小在上京长大,少不了耳濡目染,学一身纨绔子弟的习气。这样一来,要怎么同你相识相遇?”
“……”
这两个月下来,谢南枝已经学会选择性地忽略他的话,正要当做没听见,结果又见梁承骁看了他一眼,揶揄笑道:“不过道德水准低点也不是坏事,说不定到了那时,孤在倚红楼就对你一见钟情,当晚就抢回东宫做夫人,如今指不定孩子都有了,哪还有现在这漫长的考察期?”
谢南枝:“…………”
马车正好到达宫外,谢南枝没再给此人一个眼神,理了理衣裳,自己下车了。
梁承骁笑起来,紧随其后走下马车,跟着他走进了宫里。
—
纪闻今天没有同梁承骁一起上朝,在门口看见谢南枝时,着实愣了一下,随后两道眉毛差点惊飞到娃娃脸外头去。
“谢公子!”他大喜过望地把手里的笤帚一扔,欢欣道,“您回来了。”
这段时间谢南枝不在宫里,他们太子爷周身的气压一日比一日走低,搞得他进书房的时候是先迈左脚还是先迈右脚都要提前掂量两秒。
此刻的谢南枝在他眼里简直自带圣光,跟下凡的菩萨没有区别。
谢南枝从下车起,就意识到了梁承骁拐骗他回宫的险恶用心,然而人已经被叼进了狼窝里,说什么都晚了。此刻看纪闻这副拎着笤帚,勤勤恳恳扫地的模样,微妙地沉默了一瞬:“纪大人这是……”
说起这个,纪右卫顿时来劲了,正要辛酸悲戚地同他诉一番苦,结果一抬眼就看到了他身后跟着表情似笑非笑的太子爷,倏尔背后一激灵,出口的满腹牢骚硬生生变成了一声咳嗽,欲盖弥彰道:“没什么,我看这地……挺像个地的,我扫一扫,扫一扫。”
谢南枝不知道太子殿下在背后正大光明地要挟人,略微扬起眉,就看梁承骁走上来,不紧不慢道:“无事,孤前两日让他蹲一只藏起来的兔子,他在洞口守了几天,连个影子都没见着,非要孤亲自来逮。所以叫他扫两天地,练练眼力见。”
这话乍一听没什么不对,但仔细推敲起来到处都是问题。
谢南枝拒绝继续往下深想,饱含同情道:“原来如此,那就辛苦纪大人了。”
纪闻:“……”
在纪大人心如死灰的眼神中,梁承骁十分不给面子地嘲笑出了声。
“走吧。”他对谢南枝说,“既然到这儿了,去看看给你准备的宫院。”
—
穿过朝会与议事用的前厅,往后就是宫殿主日常起居的住所。
梁承骁平日不重外物,因此过去宫室的布局是怎样,他也一并沿用了,唯有垂拱门后的一方庭院,这一个月来不知折腾着改了几回。太子殿下每次下朝过来,都能挑出点新毛病,不是这株花木摆放的位置不对,影响景观,就是那片的琉璃瓦数量没有凑双,不是个好兆头——就连雪球睡得迷迷瞪瞪,从窝里爬出来,也要被抓起来把左右耳朵立对称了——俨然是要把这座宫院装点成藏娇的金屋。
梁承骁说:“你过去惯用的器物,起居用品,孤让他们一并捎来了。膳房做点心的御厨也是从东宫过来的,熟悉你的口味。另外有什么需要,可随时让詹事府去添。”
谢南枝看了一眼院内的陈设,不仅格局疏落雅致,处处藏有匠心,甚至在庭中芦枝树下摆了一方石桌,其上铺一层柔软的织物,方便他闲暇时读书作画。
他知晓梁承骁为了这番布置定然费了不少功夫,抿了下唇,心底某一块不自觉地柔软起来,又听梁承骁沉沉叹道:“一个月前,孤就开始着手准备这座庭院,但有人偏不领情,非要住那一个衣柜一张床的砖瓦房,还怎么劝都不听,实在让孤伤心难过。”
“……”谢南枝没想到他这时候还能扯崔郢出来拉踩一番,颇有些好笑,刚要说话,就看脚边不知从哪里滚来一个熟悉的黑毛球,兴高采烈地猛摇尾巴,围着他打转。
“雪球。”他心念一动,俯身把潦草的线团抱起来,狗崽顿时更加兴奋,伸长了脖子凑上来舔他的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