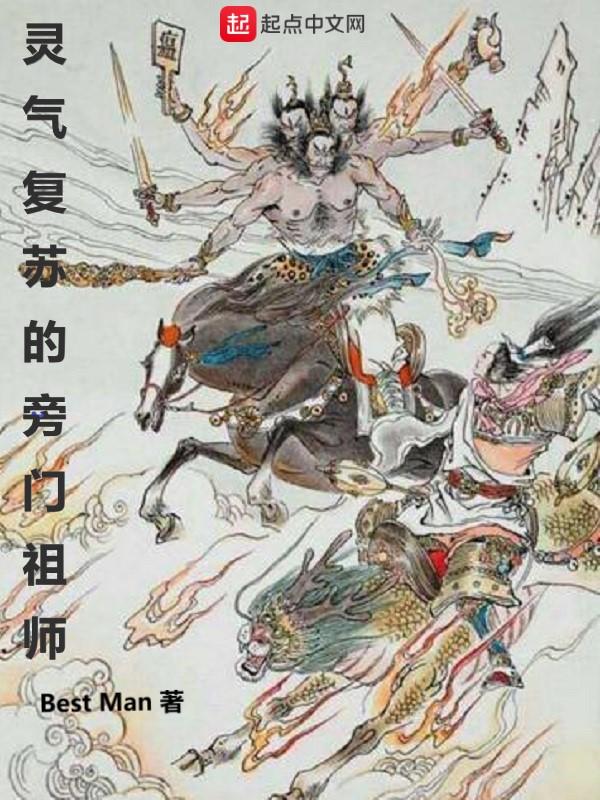秃鹫小说>误上贼船于以柔寒漠 > 第71章(第2页)
第71章(第2页)
还记得什么?
不太清楚了,只记得床头台灯的挂穗,好像在一上一下地晃了一整晚;只记得手明明受不住想把他推开,腿又忍不住要把人勾回来,手足无措;只记得自己咬着唇,绷着脚,脖颈向后仰着,发出无法自抑的哼咛的丑态。
奚听舟触电般转身看向身侧。
牧忱正睡得安稳,侧身面向着他的方向。额发有些散乱地遮住了半边眼睛,他没有穿上衣,被子随意地盖在胸口上,呼吸平稳,被子随着胸腔轻微地一起一伏。
鬼使神差地,奚听舟拿过手机,躺在熟睡的人身边,然后调出相机,就这阴暗的光线,迅速地拍了一张照片。
拍完照片,他有点心虚地扭头看了一眼牧忱,幸好,对方还睡得很沉。他把手机悄悄地塞回枕头下。
一夜的折腾不啻于进行了一场高强度的运动,奚听舟拍了照片松了一口气,又迷迷糊糊地睡过去了。
后半程他倒是睡得挺好,没再有扰人的梦境,一觉再到自然醒。这次醒来,身体的不适感好了不少,他下意识又转头去看身旁,空无一人,再看了眼房间,空空荡荡。
难道牧忱走了?
他有点懵地坐起身,想上个厕所。揉着后腰、趿着拖鞋走到厕所门口,正准备拉门,门倏地打了开来,穿着浴袍、头发湿漉漉的、脖子上挂着毛巾的牧忱跟他四目相对。
奚听舟吓得整个人顿时都清醒了。
“醒了?”牧忱在愣了一秒后,拿着毛巾胡乱地擦着自己的头发,随口说道,“刚好我让前台定了两份早餐,应该很快送上来了。”
说完侧身让开位置给奚听舟,自己走出房间去。
奚听舟手还扶在厕所门把手上,进退维艰。
进了洗手间,奚听舟才知道自己身上简直伤痕累累。镜子里淤青、吻痕都提醒着他度过了多么荒唐的一夜。腹诽道,可是牧忱怎么能像是什么事情都没发生似的?他怎么能这么淡定?
奚听舟羞于承认这种感觉,就是昨天晚上,他很爽。
虽然在那样急迫的情形下,但牧忱依然没有让他受伤,他的所有渴求都得到了回应。
同时他又有点懊恼。
一切的一切,都是药物的作用。
他羞于回味,却又不得不回味,那实在是销魂得让人欲罢不能的感觉,让人忍不住想要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