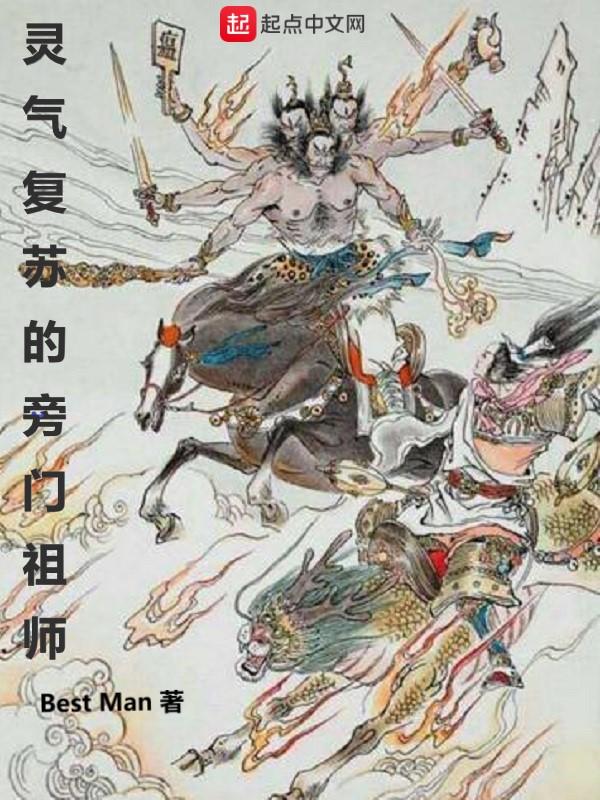秃鹫小说>戒断 by > 第89章(第1页)
第89章(第1页)
他的脸被完完整整、一丝不差地映在里面。他认真地打量自己,才发现他眼下那浓重的青,嘴角起了皮,下巴尖得病态。而他那头黑色的长发,更是毛毛糙糙。他握紧了剪刀,屏住呼吸,那些干枯的头发连同他停滞不前的生命都随着咔嚓咔嚓的声音落了地,他剪得不够齐整,但一切都是新的。“怎么突然剪头发了?”沈望听到声音,向后看去,徐斯靠着门框,似笑非笑地盯着他。“长发很麻烦,”沈望很专注地盯着他,“我能问你个问题吗?”“说。”“你那本小说,女主角的原型是我?”徐斯的笑容一滞,说:“是。”但他手上的活动不停,他从袋子里拿出三盒菜,分别是糖醋排骨、炒青菜和蒜蓉粉丝,还有一盒米饭,他很自然地支起病床旁立着的便携桌椅,坐在那木质板凳上,大喇喇地翘起二郎腿。“她自杀的时候就没有什么舍不得的东西?”徐斯拣了块排骨吃,语音不清地道:“没有吧,对她而言,都是虚假的。”沈望听了,只是哦了声,没有再说,但也支起了木凳,坐在徐斯的对面,问他:“你怎么就拿一双筷子?”徐斯道:“你要吃饭?”沈望从袋子里摸出另一双木筷,轻轻松松地掰开,对着三道菜发愣道:“有点饿。”“不吐了?”“吐了再说,难得有食欲,”沈望挑挑拣拣地吃了口青菜,一股水的味道,一点油也没放,便皱着眉说,“这店烧的中国菜也太难吃了,不知道美国的华人街怎么样。”“怎么着,你还想住趟美国的医院?”沈望道:“去纽约看看脑子。”徐斯抬头看他:“认真的?”“嗯,”沈望云淡风轻地说,“看不好的话,你那本小说就能大卖了,真人改编,昔日歌星的心声,都挺有爆点的。”徐斯沉默许久,说:“那我希望你看得好,我不差这点钱。”“要是看好了,我就跟你打官司,你抹黑我个人形象。”徐斯不屑地说:“就你那形象……”“那一圈记者不等着我想问我话?等会你找两个造型师和化妆师扮成护士进来,我得捯饬捯饬再出去见人,那帮记者就等着拍我的黑图,不能给他们机会。”徐斯吃完,盖上饭盒,看沈望半阖着眼睛乖乖吃青菜,一晃神,像是看到了二十年前的沈望。那时候的沈望也是这般表情,乖顺漂亮得像个玩偶。但沈望意识到了徐斯那缥缈的眼神,皱着眉掀起眼皮道:“听见没有?”徐斯回了神:“知道。”果然还是不同。等沈望吃了三片青菜,一块排骨,便露出些反胃的表情,皱着眉很难受的模样,但到底没吐。徐斯叫了护士重新给他戳针,护士戳针的时候嘱咐他最好把戒指给脱了,免得血液不通,沈望盯了会那银色的戒指,说,没事。徐斯坐在旁边写文稿,而沈望就跟望夫石似的盯着那枚戒指,看得徐斯都忍不住皱起眉。“看戒指还不如看人。”“他又不想见我。”沈望磨着戒指说。“你继续死皮赖脸地凑上去呗,一哭二闹三上吊。”沈望瞪了他眼,又很快泄了气:“我总是说话不算数,每次和他说我会变好的,但都没有,他应该对我很失望。这次我想真的变好了些,再去找他。”“精神病院够住你十年八年的,谁等你?”“……”没有期限的等待。顾重也许早就另觅新欢了。他的爱人是个那么好的人,喜欢他的人那么多,只要顾重愿意施舍一点点的爱意,那些人就能甘之若饴地等待他放下心里的结。他越想越难过。徐斯补充道:“但他还在新西兰。”“你怎么知道?”“我每天路过花园,他都在。”“花园?”“就你窗口对着那个小花坛,他一直坐在导演过失杀人并且销毁证据的言论属实吗”、“对于裴章导演聘请律师告您诽谤您怎么看”、“听说您在新西兰因情自杀”……他明明在直播里说得那么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