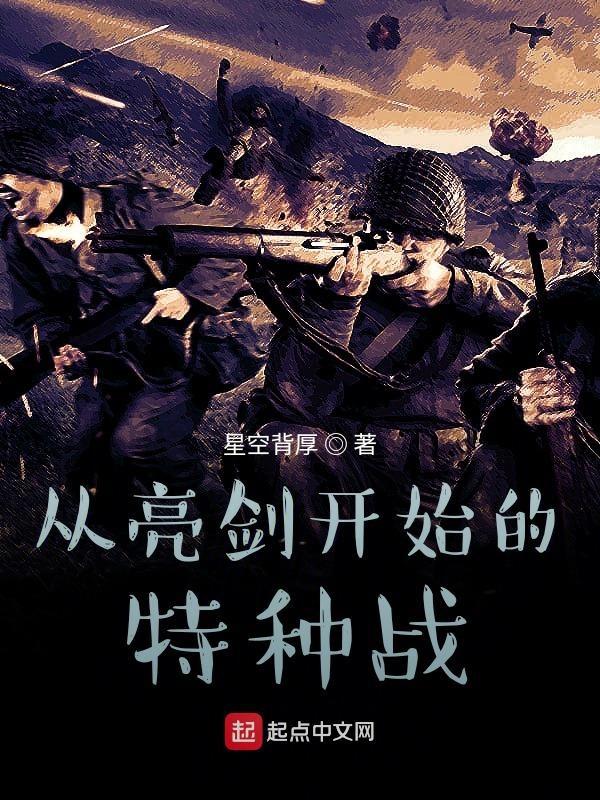秃鹫小说>师尊重生成反派白月光 > 第172章(第1页)
第172章(第1页)
封澄闭了闭眼睛:「剑修正道,我已走得腻味透顶,所谓灵脉修为,虽是累赘,却也多蒙师尊费心,入了彭山,想来数年修行也随之而去了,就算在此处还了这几年师徒恩义。」
「日后封澄所做之事,与赵负雪再无瓜葛。」
刹那间,赵负雪惊觉封澄将做之事,脸色陡然一变,可终究晚了一步,长生被她夹在指尖,一声脆响!
轻薄的剑身零零散散地碎了一地。
封澄不看他,她站起身来,意意思思地挥了挥手,便转身,打算一跃而下,陡然间,却有一道灵流猛地捆住了她的双足,凝上了一层坚不可摧的霜。
她愕然低下了头。
赵负雪平静道:「这并不是你一人自作主张之事,我说了,回去。」
被束缚的感觉令封澄从心底生了一份惊惶,她也顾不上赵负雪能不能觉察她身上魔气了,一震便震碎了足上束缚,口不择言道:「都到了如此地步,你上赶着来做什么!我说不认你了!」
回答她的是赵负雪森冷的寒意。
封澄的剑
是赵负雪一手教来的,平素自然也少不过师徒二人的对练,可赵负雪从来点到为止,连点寒气都未叫封澄尝过,直到此时此刻,正面与赵负雪对上,封澄才隐隐惊觉,所谓天下第一剑修,绝非浪得虚名。
即便重伤,剑剑亦是不可阻挡之势,封澄赤手空拳,剑早已断掉,此时藉以傍身的,只有仓促间抓下来的木棍。
封澄被逼得恼怒,牙一咬,也认真起来,谁料赵负雪重伤,灵力迟滞,她还手一击,便将人手中的长剑格住。
她盯着赵负雪的双手,鬼使神差间,望见了他的双眼。
他的双目中燃着几乎能称之为愤怒的神色。
赵负雪这样冷清的人,也会为人动气,为人愤怒吗?封澄想。
赵负雪冷道:「歧途易入难出,血修逆天而行,绝无善终。」
封澄倍觉荒谬:「哈?您老觉得我不知道?」
铿然一剑,封澄将衣袖一甩,随即往外一送,她道:「是非对错若有那般界限分明,这世道还要师尊做什么?还要我做什么?」
赵负雪闻言,顿了顿,封澄自觉失言,偏过头去,道:「总之你别管了,我要走我的路,与你一点儿关系也没有。」
说罢,封澄将手一挥,紧接着,赵负雪猛地变了脸色——锁灵香!
封澄头也不回道:「剂量微小,一息之瞬,想必赵家也不会叫师尊孤身出行。」
这种香料,只有边关的几个寨子有存,些微都是不世之珍——封澄怎么会弄到这种东西?
她头也不回,念咒将人缚住,转过身,一跃而下。
***
刘润看着摆在眼前的奏摺,勃然大怒,甩袖将东西呼啦啦地掼了出去;「这群血修嚣张至此,简直大了狗胆,无法无天!」
霎时间,殿中霎时跪倒了一片,被奏疏砸了脑袋的大臣头也不敢抬,小心翼翼道:「回皇上,实乃事情有变。」
姜徵不动声色地看向了那大臣。
大臣擦了嚓冷汗,小声道:「从前血修虽是作乱,可并不成规模,几条杂鱼,杀了便是。可前些日子……」
刘润余怒未消地看了他一眼。
「……有一血修横空出世,将四面血修收服于彭山,如今,已渐成规格了。」
血修的等级意识如同野兽般强烈,从前彼此不服,四处争斗。刘润怔怔道:「那,天机所无可奈何么?尊者拿他们没办法么?」
大臣无奈地叹了口气:「尊者前些时候闭关,京中天机师,能与之相抗者寥寥无几。」
刘润一拍龙案站起来:「调人!调人!旁处天机师是吃干饭的?边关的仗也别打了!叫天机铁骑来剿匪——封澄呢?叫她去带人!!」
此言一出,四下死寂,刘润察觉不对,皱眉道:「怎么?」
大臣头也不敢抬,小声道:「……皇,皇上,反叛血修,正,正是封澄。」
咚地一声,刘润愣愣地摔在了龙椅上。
他好像梦游一样,不可置信地喃喃:「……反叛?她?她,朕不过是命她留京几日,连军职都未削,她,她怎么就敢反了?」
大臣不敢吱声,有一人却愤愤不平道:「她早就不安分!仗着杀了几个破天魔,趾高气扬,谁也不放在眼里。皇上,依臣之言,就不计代价,把人抓来杀之示众!京城这么多天机师,难道还怕一个彭山吗!」
姜徵看着他,认出此人面目,挑了挑眉,道:「胡郎中,彭山凶险非同寻常,不计代价四字说来轻巧,实则做起,血雨腥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