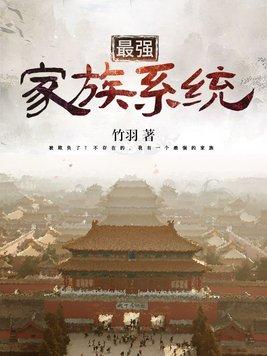秃鹫小说>月照时春 > 那要怎么卖(第3页)
那要怎么卖(第3页)
钟五心中更是厌烦。明明他媳妇儿年纪小,他们还想两个人多过一段这样不被小孩侵扰的生活,一点也不着急。
但也不知道郑秋娘怎么解读的,愣是解读成他们两人迫切想要生一个孩子。
他给他媳妇儿夹菜,她说,他媳妇儿给他烧水,她也说,甚至于晚间他们回屋,她也要不尴不尬地说上一句。偏偏又无视其他回屋歇息的哥哥嫂子们,眼珠子只盯着他们两口子。
郑秋娘说的次数多了,就算钟五和江衔月都不怎么提孩子的事儿,家里人也都误会他们急着要孩子。
甚至陆氏还找钟五说过两回,劝他别逼得太紧,别给他媳妇儿太大压力,钟五只能面无表情地听着,连解释都不好解释。
有一次吃夕食的时候,他媳妇儿吃好了,看三嫂抱着静儿吃饭不方便,就接过来抱着逗她玩儿,三嫂刚道谢,郑秋娘就当着大家的面劝他和他媳妇儿一起去医馆找大夫看看,还说什么“虽说年纪轻,但既然着急,不如早些去找大夫瞧瞧,有什么毛病也能早点发现,早点解决。就是没看出来什么病,早点把身子调养好了也好怀个孩子,也不用整天抱着侄儿侄女儿眼馋……”
他和他媳妇儿当时就愣住了,四哥的脸都成黑炭了,要不是三哥和老六开个玩笑混过去了,他都想拉四哥出去谈谈。
那一回之后,可能是四哥跟郑秋娘说了什么,她倒也不捏着孩子这回事不放了,但又开始折腾起别的。
也不知出去串门子的时候听谁胡说了什么,回来就故意跟他媳妇儿说一些没边没影却又令人遐想的话,话藏一半露一半,有时候他听不过去,都光明正大讲清楚了,郑秋娘还掩着嘴假惺惺地笑着给自己打圆场,说些什么“是某某某说的,也不知道是真是假”,“我也是听人说的,想来老五不是那样的人,五弟妹可别多心呢”,“唉,都是他们瞎说的,我就说怎么可能是真的呢”,听得人浑身不得劲儿。
郑秋娘的这些作为,直接导致他哄媳妇儿的难度成倍增加。
为了自证清白,他连过去都谁来家里给他做过媒,他以前在路上跟哪家婶子大娘打过招呼,甚至从穿开裆裤到现在都交了哪些朋友,跟谁一起干了哪些好事哪些坏事,都一一交代了。
但郑秋娘说了那么多人,有一些他根本就没印象,郑秋娘也说得跟真的一样。
说他在路边对谁笑了,帮哪家嫂子挑过水,帮哪个寡妇砍过柴,给过哪个小娘子果子山货等等等等。
他媳妇儿问他这些的时候,他都一脸懵。
平心而论,钟五认为自己认识江衔月之前,是个比较严肃的人,对着自己爹娘和兄弟都不怎么笑,更别说对外人笑了,当然江衔月和江家人是个例外……他只想让她当内人,从不把她当外人。
至于挑水、劈柴、给果子山货这些,就更不可能了。就是有果子山货,他也都拿去卖钱或者拿回家孝敬爹娘了,哪会拿着去给不相干的人,当然江衔月和江家人在他眼里自始至终都不属于不相干的范畴。
钟五翻遍自己的过往,也只记得自己就给过应雄家的俩娃果子,但应雄是他的发小,他的娃也应算在子侄之列。
他现在对郑秋娘算是深恶痛绝,虽然原来他就不赞同四哥娶她,但那时候她话少,除了傲气,行事上有些拎不清外,为人还算正派。
可如今呢,净学些长舌妇的勾当,搬弄是非,无中生有,还专门盯着他们夫妻俩,实在惹人厌烦,他是真的有些同情四哥了。
若是郑秋娘手段高超,挑拨的话能说得滴水不漏,他也能赞她一声高明,但从她目前的行为看,真的是明眼人看得见的愚蠢。
好在他媳妇儿明理,不曾真的计较这些,还说女子孕期脾气会跟平日里有些不同,两个人躲着她点,那些酸话就当没听见。
钟五想起来就觉得生气,也幸亏那是他四哥的媳妇儿,那要是随便哪个不相关的人,他都想一拳打上去,让他好好醒醒脑子呢。
-----
江衔月不知道片刻之间钟五脑子里就过了这么多东西,但看他一脸郁闷的样子,她拍他的手,“快起来,去买糯米纸,不然就扎些草把子,天气热,不隔起来,怕糖化了黏到一起去。”
“我昨天就买了的,你歇着,我去做。”钟五说着,就去洗李子,熬糖稀,上手做起来。
江衔月不放心,过去看,见他只看过一次就做得像模像样的,也不管他,自己又回屋里去画团扇。
这是她想出来的新主意,圩市上卖折扇和蒲扇的很多,卖团扇的就只有县城有,且大都在大商铺里,做工比较精致,卖价也高,倒是在乡下还没见过卖这个的。
她手里刚好有不少素色绢罗,还有之前买的两匹浅色夏布,用来画这个正好,就和钟五琢磨着做了几把白扇。
做出来很是不错,画上画既漂亮又雅致,她呼扇着试了试,风力虽不如蒲扇大,但胜在小巧轻便,也挺结实耐用。
她平日里无事便画,如今也画了有六七十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