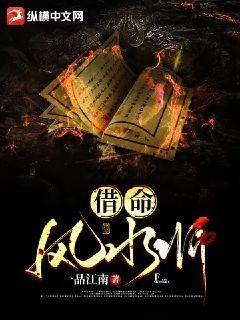秃鹫小说>秦皇汉武唐童现代留学日常免费 > 6070(第5页)
6070(第5页)
“你们说他是不是在攒怒气值,等我打猎归来攒足力气喷我啊?不然怎么一句都不说呢。”
“我明白了,他是还没拿我当主君呢。”
刘彻大概有事,没看消息。嬴政打了一串省略号。
李世民把手机收回空间,一下子干劲满满,自己一握拳,“没关系,迟早叫他拜服,认我为主!”
等房玄龄和杜如晦到,他再请魏徵过来,不提刚才打猎半途回来的事,正经跟他们商量事情。
“我从去年到今年就没停过上书,每次禀报庄稼的长势,都要明示暗示提一提我转武职的事,但一直也没回音。你们说他是不是根本没看?还是我这年纪实在是不合适。还有什么办法没有?”
魏徽还不太清楚什么情况,房玄龄向他略略说明。魏徵一哂:“说不定真没看——就算看了,谁会让你这个年纪的人去带兵?”
“所以问问你们有没有办法。”李世民也是死马当活马医。如果能在明年杨玄感谋反前有一支兵马在手,那时就有机会建功了,之后也才有腾挪的余地。
三个人都没说话,各自沉思起来,但这事还真的难。
魏徵看看另两人,心中生出不服之意。他看得出来,李二郎对这二人十分尊敬器重,对自己——不清楚,有点怪,他说不上来,并没有轻慢,但就是不太对劲。
他难道比他们差么?倒是要看看他们解决不了的事,他能不能做成。
一念及此,魏徵双目微闭,捻须沉吟,取笔墨涂写起来。李世民探身过去看,被他大袖一挥,掩住不给看草稿。李世民只好悻悻地缩回去等着。
房玄龄与杜如晦相视而笑,他俩旁观许久,同样觉得二郎对魏徵有点奇怪。某方面来讲与对他们是差不多的,有点自来熟的亲切,另一方面好像又有点说不来的不同。
魏徵则是被掳来的并非自愿,现在又不想着跑,又不琢磨告密,在田里忙得挺高兴,只是对上二郎就拉下脸,观方才的举动,其实却也挺亲近的。
房玄龄瞧着李世民还在努力盯着魏徵的纸笔想偷看到内容,魏徵边思考边涂涂改改,都注意不到别的,便用唇形对杜如晦暗语:“玄成其实挺喜欢二郎的吧。”
杜如晦微微点头,同样用唇语回答:“谁会不喜欢二郎呢。”
魏徵这一写还挺久,李世民从想偷看先睹为快,到放弃了转而跟房杜小声聊天,再到聊得声音大了被魏徵发怒赶出去——他都还没写完。
李世民出去气得跺脚,小声说:“我就不该让他们把这老道带回来!”
杜如晦轻咳一声,“二郎,你可以大点声说。”
“我就不该……”李世民大声吵吵,只是说到最后几字时又轻声下去了,“……让他们把这老道带回来。”
屋里一点动静都没有,魏徵应该没听见。
许久,才听见里间一声击案,李世民抢步进去,果然见魏徵正捻须摇头晃脑地在默读自己文章,显然是成了。
“我瞧瞧。”他一把抢过来,魏徵读了一半被抢走,胡子都拈下来数茎,气得摇头,向房玄龄控诉:“你们就这样认他为主了?看看这无礼的模样!”
“哈哈,二郎还年少,只是活泼一些而已。玄成莫气,莫气。”
房杜二人一起顺毛,魏徵板着脸坐在一旁,看似生闷气,实则在观察李世民的反应。
李世民如何呢?他越读越觉得,只要杨广不是真的看都不看,他可能还真有戏!
魏徵是以他的口气所拟,上书先不言事,而是先拍了杨广一通马屁,又把如今在关中、洛阳和江都扩散出去的嘉禾作为杨广的政绩给吹捧了一遍。
刚刚攻辽失利的杨广想必会很开心吧。因为这毕竟是实实在在的政绩。以往只偶尔出现的嘉禾,现在江都已经满目皆是——至少是他行宫和出游所至之地,看到的都是亩产超过三百斤的水稻,虽不及试验田,但也比真正的平均产量高得多。
这已经不是祥瑞了,这是天命。所以一次失利根本不算什么。
魏徵根本没提攻辽的事,现在虽然还没有撤军,但失利的消息一再传来,大家都晓得必是败阵的结果了。这事提了是自寻死路,杨广受不了这样的打脸,哪怕是帮他开脱也不行。但是字里行间,偏偏处处能觉出在给他开脱。
然后话锋一转,他拿李世民之前的文书看过,这会儿模仿得也像,学着他惯常的语气表达了嘉禾功成,自己不愿再行田舍事,想要做天子的冠军侯的意愿。
又自恨年少,不能为天子带兵,痛陈如今军中不力,士卒不能为天子尽力,自请入军中向宿将学习,将来为天子练兵。
言语间仿佛不经意又替杨广开脱了一层——并非他用兵失败,而是兵卒不行啊。
李世民的表情很难形容,跟魏徵想象得不太一样。
确实有惊喜,但很快就消失了,甚至有点扭曲。半晌,等他把文章给房玄龄和杜如晦传看,自己抬起头来的时候,更是有种欲言又止,一言难尽的样子。
怎么了?魏徵自省,他写得很好啊,有错吗?
李世民幽幽地道:“原来你说话这么好听啊。”
魏徵毫不客气地哈哈两声:“在下学纵横术多年矣。”
言下之意,这说话的艺术是他本行,还用你说吗。
李世民欲言又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