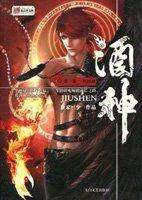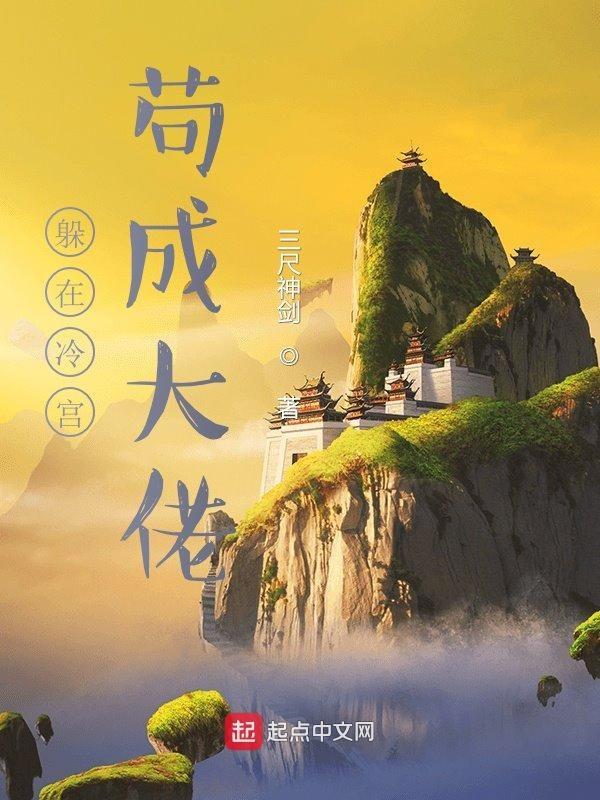秃鹫小说>飞鸟尽良弓藏兔死走狗烹什么意思 > 第82章(第2页)
第82章(第2页)
……
靳邵比她想的更来劲,她想不通什么缘故,只是每在抽出一丝理智告诉他明早要赶飞机时,都会被他作耳旁风压过去。
来之前说要在床上好好挑挑口味,真正上了床又无暇顾及,凭本能摸索的花样比精心钻研过还熟练,黎也几次想停,刚蹭开就被他按着腰拽回来。
她一直不知道的是,靳邵对她喝多这时候有种难说的瘾,最早得要追溯到上学那会儿,光是看着她理智跟酒精作激烈斗争,就躁得不行,有种不想又不可控制地一点点撕裂表面的严谨冷傲,皱着眉,哈着气,哪里都变得容易刺激泛红。反抗不彻底就像迎合。
到最后两个人都烫得不像话,夏夜里汗涔涔淋一身,发丝沾黏皮肤,神志早就离家出走,亏得那傻逼还能凑她耳边讲骚话,揪着她汗湿的脸颊笑:“你得亏是遇到我,个二两倒的货,让别人捡了可怎么办?”
黎也眼睛都睁不开,还是气得凑前去咬他,他笑不停,拎着她后脖子分开,追吻过去。
-
这晚黎也完全没有入睡的概念,被靳邵喊起来赶飞机时,魂还在天上飞,大醉一场,做什么都慢一拍,她洗漱时,他已经在收拾两人东西。
终归是磨磨蹭蹭地卡点赶上,一上飞机她连时间概念都没有了,除却走在路上的时间,她都在睡觉,一坐就睡,根本不关心飞到哪,再转了火车坐到哪,蒙头跟着身边人走。
再有意识是一觉醒来,他们坐在火车站外叫的顺风车上,车里没有别人,或是只剩下他们两位乘客。
因为路途变得颠簸,她在震荡中醒过来,离开身旁肩膀,看见窗外映入眼帘的、越发熟悉的街道老建筑时,心情经历极速的上升又下坠,迟迟平稳,她睁眼问旁边:“怎么回到这儿了?”
车子也终于在摇摇晃晃中稳停,下车时靳邵看了眼手机,十点多,他没回答黎也的询问,拽着人往街路前方走,“先吃点东西垫肚子。”
两人都穿得休闲随性,以至与落后古旧的环境并没太大的割裂感。近午时的大街路上没什么人,这还是那个冷热极端的小地方,烈阳辣得烧脸,吸进鼻腔像股蒸笼里冒出的热气儿。
很奇异的感觉,上一次他们距离这里很近,却闹得那么不愉快,根本没有回来看看的机会,而黎也再想到这,已经是几年前发的一场疯。
新城区距离天岗这块只有十五分钟左右的路程,同在小城,这里跟进时代的步伐就偏慢了,个别老街旧房还能看出些卡在旧时代的齿轮中顿足不前的影子,平凡,荒芒而宁静。
那旧房中,就包括了他们走进的千里香馄饨店,门口招牌已经不见原来鲜亮的颜色,字儿都快在晕散的淡红中看不清。
客人一进门,椅子里挥扇站起的是个三十来岁的女人,招呼他们坐,问他们要什么,再一嗓子招厨房里的丈夫出来。
憨厚壮实的店老板一见落座的人,就眼熟盯着横看竖看,被女人拍了回神,脑子也一灵光,指着靳邵口吃,你你你地,你出来靳邵一声字正腔圆的胖哥:“现在日子混挺好,娶媳妇儿还当老板了?”
胖哥一拍手,说是嘞!女人抓着他问什么人呀,他脑子还是钝,却比以前好多了,能憋出来句老朋友。
靳邵就问他:“你们夫妻俩管店,你娘回家歇了?”
他说话要打手势,摸摸脑袋再指到胸膛,却不知怎么口述,只说:“身、身体不好啦!”
他眼睛亮,看见黎也,早想问他俩,这当头被老婆推着往里走,说赶紧给人做吃的去!临到帘门前,靳邵又说了句:“一碗别放葱花。”
“诶哟,”女人听了笑盈盈,“馄饨没葱花,香味都少一半儿!”
他手在旁边人的肩头一搭,扬声笑:“我老婆不吃。”
女人意味深长地笑,马上喊了声土话提醒厨房里头,再去给他们开了吊扇。先知道是老朋友,于是自来熟又拉着两人聊了些许,店里也没别人,话题敞开,问小两口多大了,住哪儿呀,什么时候结的婚呐,有孩子没……还是被喊了声帮忙,才恋恋不舍地钻进厨房。
对坐的两人颇有些被长辈关怀的紧切,人走好一会儿,才对视一眼,笑起来。黎也肘撑着桌前倾,他也凑前,她挑起眉,说:“我不止不喜欢葱花,我还不喜欢馄饨。”
“这么巧?”他听后也笑,指腹伸在她脸上轻蹭,说:“我也不喜欢。”
少时候总觉得时间长久,却又紧密,分明每天都在相处,每天那种时刻又在很快地过去,彼此留住彼此的方式很少,可能是一句“你今晚别上楼睡了”,或是一句“明天还去那家馄饨店吧”,什么样都好,能待在一起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