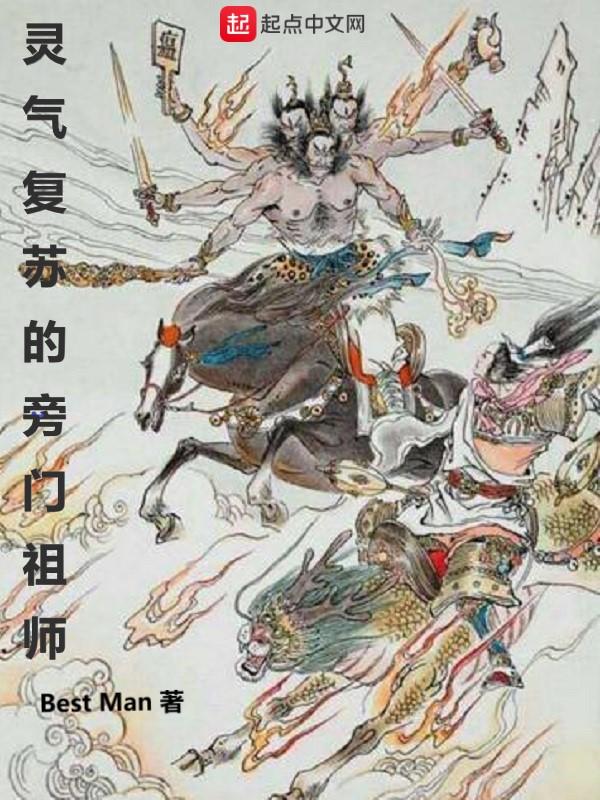秃鹫小说>我竟然拿了虐文剧本呀呼推荐 > 第5章(第1页)
第5章(第1页)
因着岑锦年是幺女,所以岑松夫妻二人对她向来宽容,她一问裴舟的事,柳元容便告诉她了。不过这些事情也没什么好隐瞒的,只是说起来,年代有些久远罢了。据柳元容所说,裴舟的太太奶奶是岑锦年的太太奶奶的姨家表妹,两人自幼相识,感情甚笃,而裴舟的太太奶奶因着某些缘故,于岑锦年的太太奶奶有相救之恩,所以岑家便欠了裴家一个恩情。不过因着很多年前裴家便搬往了西北,又一直久居漠县,且从未提起过此事,这个恩情便一直留了下来。虽说已隔多代,时间久远,但岑家毕竟是重诺之人,别人不提起,却也一直放在心上,更别说两家还一直偶有书信来往。如今裴家突遭此变,裴母亦来信托孤,不论于情于理,岑松都该应下。岑锦年得知完这些,只觉唏嘘不已,不得不说,裴舟确实有些惨了。看来以后她得多对裴舟好一些,就当是帮她的太太奶奶报恩了。这日是十五,岑锦年早早便起来准备往岑老太太院中去请安。此时天还未大亮,只隐约瞥得见天光而已。已经下了好几日的雪,今日晨起竟然发现雪停了,倒也是好事。不然每次出门,脚下的靴子总容易被积雪弄湿,大冬天的又这般冷,一个不小心就很容易着凉。前两日便听说二叔家的三姐和四姐不小心染了风寒,已经咳了几日,如今想来,今日去请安的小辈可能也就只有她了。思量间,她已经来到了岑老太太所居的瑞竹院外,正当她抬脚往里走进时,恰好瞥见远处有人打着灯笼正往这边走来。心中不免疑惑,三姐她们何时这般勤快了,生病了也要过来给祖母请安?天色昏暗,太阳还没有升起,又因着离得远,所以她瞧得不是很清楚。想了想,还是觉得在这等一会儿她们比较好,岑锦年随即停下了脚步。待远处的人走近,岑锦年瞧清了来人后,顿时满眼惊讶。怎么是他?裴舟瞧见她,立即嘴角含笑,朝她颔了颔首:“锦年表妹。”嗓音还是一如既往地好听。岑锦年见状,赶忙敛住了眼中的惊讶,扬起笑容,说道:“裴舟表哥,好巧。”“确实巧。”裴舟脸上笑意未减。“裴舟表哥也是来给祖母请安的吗?”裴舟点了点头,“嗯。”那倒是有心了。岑锦年又往他身旁提着灯笼的人看了一眼,此人身形颀长,面色稍冷,甫一见面便莫名给人一种压迫感,即便他已经刻意收敛了身上的冷意,但还是令人想远离。只看了一眼她便迅速将目光收了回来。这人站在裴舟身边,二人倒是形成了鲜明对比。裴舟脸上笑意温煦,他身旁这人却是如同冰山般,寒不可近。之前便听说裴舟身边时常跟着个形影不离的人,名唤高冽,是他的护卫,想必此人就是了。没有多说什么,岑锦年随即朝裴舟道:“外头冷,我们还是快进去吧。”“好。”话音一落,几人便一同往里走了进去。来到屋中时,岑老太太也刚刚起身,正在里屋洗漱,因而他们二人便坐在了厅中等候。屋中烧了地暖,乍然从外头的寒风中走进,这室内暖洋洋的,叫人也不禁变得懒洋洋起来。今日本就起得早,如今这屋里头的温度又过于舒适,等了好一会儿岑老太太也还没有出来,岑锦年便忍不住犯起困来,下意识便想打哈欠。可当她嘴巴刚张开,又豁然想起裴舟还在这儿,只得连忙将嘴合上,生生将这哈欠给咽了回去,同时还装作漫不经心地往裴舟那边瞥了一眼,幸好裴舟正垂着头,不知在思索什么事,也没有注意到她这边。唉!她这人在家里头一向随意惯了,因而倒也不大注意这些。如今突然多了个表哥,看来该注意的还是得注意一下。方才没怎么在意,这会子发现这里就只有她们二人,时间长了总觉得有些尴尬。想了想,岑锦年还是觉得应该适当开一下口,随便聊几句也比对着干坐好。随后,她便弯了弯唇,一双大大的杏眼稍稍扬起了个弧度,笑意尽显和善:“表哥在家中可还住得惯?”、摔跤坐在岑锦年对面的裴舟突然听见这话,原先微垂的头慢慢抬起,朝她望去,脸上神情还是那般柔和。“多谢表妹挂念,一切都好。”岑锦年含笑点了点头:“那便好。”气氛再度沉默下来。过了一会儿,岑锦年再度开口:“若是下人们有什么怠慢的地方,表哥不用多虑,只管训斥回去就是了。若是这般他们还不改,表哥也只管来找我,我定然是不能让表哥在家中受委屈的。”毕竟这个年纪就没了父母,一个人千里迢迢地跑到京城来投奔,举目无亲,还是怪可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