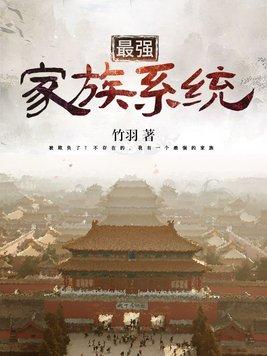秃鹫小说>我的诡异人生讲的什么 > 第1545章 诸我归一三(第1页)
第1545章 诸我归一三(第1页)
苏午神色忽恍。而那道站在窗边,观察着窗外雨线的模糊身影,在此时逐渐变得清晰,它对照着苏午的模样,像一团沸腾的水液般变化着,最终将自己变作了与苏午别无二致的模样。它身上有着苏午‘诸我之一’的因果。但是它不是苏午。元皇、大天,以及那属于苏午诸我之一的因果气韵,在它身上相继浮现,又统统消寂。“还记得这里是哪里,记得今天是什么日子吗?”一张沧桑古老的面孔覆盖住了那道诡异身影面庞上苏午的五官——大天咧嘴笑着,发出苏午的声音,与距它只有三步之远的苏午如是问道。棺椁内,其实没有元皇,亦没有苏午的诸我之一,只有大天。亦或者说,棺椁之内,既有元皇,又有苏午的诸我之一,只是此二者,终究完全被大天合为己用了。苏午被外面的大天一路追迫至这元河尽头之时,内心已然有了此种判断——棺椁之外的‘大天真形’,浑如一座无尽厉诡堆积而成的坟冢,宇宙洪荒亦不过是这座陵墓的一部分而已。而这座坟冢的主墓室内,却没有棺材停靠。大天这座坟冢,并非无主之墓——它的棺椁其实就停留在元河尽头,就是元河尽头的这座漆黑棺椁。在更久远的岁月以前,元皇陨灭在此,它尸身的绝大部分化作了元河及至众生,但剩余残骸却被大天的力量浸染了,逐渐成为大天的一部分。及至后来,苏午的诸我之一踏临此间,为此间带来了诸多变数。因那些不可测的变数,大天将元河尽头的自身隔绝于外,放出‘登仙’的诱饵,谋划了数万载,编织起这一道谜题,一切种种就是为了等候如今的‘破题人’出现。情关、生死大关,就是这道题目本身。苏午又能否交出答卷?他环视这间素净简洁的房间,尘封的记忆一点点被翻出来,在脑海里浮漾——这间房子,是他在上大学的时候在校外租住的一个小房子。房间衣柜里的那些女性衣裙,以及床头上摆放的那些可爱玩偶,其实是他当时交的女朋友留在这里的。而这些事情,都已经是很久远很久远的过去了。哪怕他稍一转念,脑海里就能浮现出当时女友的容貌,但他的心底却不再会因此而生出任何波澜与悸动。但他看向大天一阵阵扭曲着的身形倚靠的窗台,看着窗外那阵断断续续的雨线,他的神色终于起了些许变化,有些难言的恐惧与悲伤酝酿在他心底,最终都变成了喉结微微滚动的那几下。苏午已经记起来了今天是什么日子。在这场雨下起来之后,再过将近半个小时,家里的亲戚就会到他的学校找他,带来父母的死亡通知书。“想起来了?”大天咧嘴笑了起来,它那张苍老得让人厌憎的面容,忽又化作了苏午的五官,它顶着苏午的脸,同苏午说道,“只有无知蠢物才会觉得,所谓‘情关’只能是男女之间的情情爱爱。那些所谓男女情爱,在我们眼中,却是最可以轻易放弃的东西。而你的真正情关,便是今时的‘父母之爱’。你能闯破这重关卡么?——今天,正是我们的父母——苏铨与郑春芳死亡的日子,时间往后推转半个小时,他们就将彻底死去……不过现在,时间未到,他们还好好地活在这个世上……苏午,你可要同我去看一看,我们的父母?”苏午诸我之一的因果缭绕在那道扭曲的形影上,它向苏午提出问题以后,面上便浮现出了戏谑的笑容,等待着对面苏午的回应。苏午沉默着,心脏微微战栗。他没有向大天询问当下这般情景,究竟是幻相?还是真实?行至此地,不论是他,还是大天,亦或是元河尽头之外的三清,都有将幻相化为真实的能力。真幻虚实于他而言,并不重要。不论他视这般情景是虚幻还是真实,最终都需面临内心那道真实无虚的关槛。在大天的目光注视之下,良久以后,苏午口中终于发出干涩沙哑的声音:“带我去……”他话音落地,窗边的大天面孔上戏谑笑意更浓,它没有任何动作,四下里,却有五色斑斓之光景象扭转,将当下这间雪洞般素净的屋室吞噬去,继而漆刷、粉饰成一个阴沉的雨天。雨天下,高楼林立。不见一个行人、一辆汽车穿梭的十字路口边,那两道让苏午魂牵梦萦、触不可及的身影,就站在彼处,静静等候着路灯由红转绿。他嘴唇翕动,喉咙里却没有发出任何声音。他原本以为自己此生再也不可能与父母照面——于华山人道根脉处,父母的因果已经彻底湮灭了!可在今下,他无从奢想的情景,真正成真!“这只是一重幻相而已,打破幻相,粉碎真空,你便能统谐诸我,将苍生背负起来,乃至再造新天。”大天站在苏午身边,它长得与苏午一模一样,甚至本身就留有苏午诸我之一的完整因果。它轻轻言语着,像是在劝告苏午,但这番劝慰的言辞,却将苏午的心神不断拖入无底的深渊。,!境由心造……眼前一切,究竟是不是幻相?苏午须问过自己的心。他看着那两道真实无虚的身影,内心所有翻腾的情绪都好似化作了驯服的小兽,依偎向那两道背向他的身影。而在此时,路灯上的数字不紧不慢地跳动着。它未曾被人刻意拨转加快,亦不曾以谁的意志变慢半分。12……11……10……9…………枯寂冰冷的黑暗环绕着那片流淌有五色斑斓之水的元河起源,元河起源之中,漆黑棺椁静静浮沉,自苏午踏足棺椁之中,至此数个瞬息之间,那副漆黑棺椁都没有异动。而元河起源之外的洪荒宇宙,已然被‘皇天真形’胸膛中伸出的那道手臂,抹平了九成。这绝灭生机的黑暗之中,除却元河起源之外,便只有彼方的鸡卵天地还在大天摧压之下苦苦支撑。黑暗中,皇天真形抵近元河起源的边缘地带。无尽厉诡高堆起的坟墓,阻隔着出入元河起源的门户,将三清本形拦阻在了其之后。三清静立于这深彻的黑暗中,它凝视着那座高堆成坟山的‘皇天真形’,继而朝元河起源之中的漆黑棺椁望去一眼,这个刹那之间,它性识中的某些猜测已得验证。它终于在此时向大天开口:“看来你并非无法踏足元河起源,实则是一直以来佯装作不能履足彼处。元河尽头的棺椁中,埋葬的存在是你。看护这棺椁的存在,是你。归葬一切,毁灭宇宙的那位,也是你。吾从前也被遮瞒了,竟未曾发现,其实你距离‘诸我归一’的境界,比其余任何一切存在都近的多。你与此境,只差临门一脚了罢……”“归葬万般之后,我方能统合诸我。”大天那坟土陵墓似的身躯之顶,紫红天根绞缠成那张沧桑古老的面孔,它俯视着三清真形——三清回首过往,蓦然发觉,自己所谓与大天分庭抗礼、相互寄生的那般辉煌局面,其实也不过是大天想要如此,想要令天下万众以为真实情景就是如此而已。而它实与天下万众别无二致。——一直都是在这‘天命’造作之中存活,从来不曾真正跳脱出去!天命!天命!天命!更深彻绝望的黑暗从三清性识之中涌溢而出,而在这个刹那,那道抹灭宇宙万般存在的紫红手臂,朝着三清本形盖落——嗡!无声无息间,三清游离于深彻黑暗中的那一缕道炁游曳着,贯连起了彼处的鸡卵天地——它的本形被那一缕早已提前准备好,预防最不测情况的道炁牵引着,悉数回向彼处鸡卵天地!“真难啊……”诸般筹谋临近尾声,大天又何尝不是在心识间一遍遍回首过往?它应对宇宙洪荒之间每一次滚滚而起的浪潮,哪一次按落潮头,又不是耗尽心力了?如三清、苏午这般存在,它应对起来,亦是千难万难!从前差点被三清掌握局面是真,今下险些被苏午成就诸我归一之道果,彻底粉碎它,再造新天,也是真!好在,这一切终将过去了……从那座恐怖陵墓主墓室里伸出来的紫红手臂,向着彼处的鸡卵天地拍击而去——那由苏午天柱超脱相支撑着、凝合了鸿蒙金座气韵,有三清、燧祖、柳飞烟存身的鸡卵天地,在这湮灭一切的手掌之下,一刹那摇摇欲坠!但它并未破碎!浑若鸡卵的‘外壳’之上,诸气流转,竟连裂缝也无!大天并不在意自己这一掌未能摧灭那重鸡卵天地——此间有无数个刹那,彼方天地能抵住他这一掌拍击,却不可能抵住无数个刹那里,它的无数次拍打。它轻轻抬起那道紫红手臂,再向那重鸡卵天地拍去一掌——正在此时,元河起源之处,那尊漆黑棺椁忽然震颤了开来,在元河起源的泉池之中掀起一阵阵浪潮,甚至已经关锁的棺盖裂开缝隙,朦胧五色凝如液体的光芒从中流淌了出来!轰隆!轰隆!轰隆!那座棺椁的震动,更牵动着大天的性识。它直接收拢了拍打向鸡卵天地的手臂,继而以皇天真形轰隆隆压入元河起源之中——那被苏午留于元河起源之中的诸我,在此时化作了一道道恐惧的刑具,诸我沾染了苏午身上流淌下的金沙气韵,因而一个个都有杀死厉诡的能力——那一道道恐怖刑具或砍、或刺、或钉、或扎在皇天真形周身各处,在皇天真形各处,留下无可弥合的、巨大的割裂伤!元河起源之地的棺椁,震颤愈发狂烈!大天早知苏午未曾汇合的诸我,随着自身踏临元河起源之后,将会爆发出怎样的威能,但比之皇天真形被苏午诸我斩裂,乃至是摇摇欲坠,它更在意的始终是那座漆黑棺椁。棺椁中的‘自我’,绝不能出任何差错!是以,大天生受了苏午演化的这诸我刑具,高堆厉诡坟土的陵墓,霎时遍布裂缝,幽沉的大天神韵从那一道道裂缝中流淌而出,却无法洗刷那些刑具带给皇天真形的损伤。,!它生受了苏午的诸我刑具,亦终于临近那座漆黑棺椁。——可在此时,那座漆黑棺椁却又停止了异动,再度陷入沉寂之中。……3……2……1……0……路灯上的红色数字刹那跳动为0,继而瞬息换作绿色。苏午的整颗心脏都被揪了起来,在他的注视之下,父亲与母亲拉着手,观察过道路两边,确定没有任何车辆通行前方的道路之后,便迈开步子,大步通过人行横道,并肩走到人行横道中间——这时,一种前所未有的危机从苏午心神间猛然爆发了开来!伴随着此般凝如实质的危机感,他蓦然侧首,看到在距离父亲母亲不到五米的位置,悄无声息地出现了一辆大巴车,那辆大巴车在空气里化作残影,发出一连串尖锐的、划破空气的爆鸣声,直撞了他的父母!“别!”“爸!妈!”苏午下意识地喊叫出声,蓬勃旺盛的金沙气韵在他喊叫之前,就从他身上流淌而出,聚集在他父母身侧,化作了一堵坚实的墙壁,以阻挡那辆骤然出现的大巴车的冲闯——“这样真地有用吗?”在他身畔,传来大天与他一般无二的声线。那满带戏谑的声音还未落下,一道指节修长、五指刚健有力的手掌、一道缠绕紫红天根的手掌、一道聚集着无数元根的漆黑手掌,叠合在了那辆化作残影的大巴车后。苏午的诸我之一、大天、元皇三者的气韵叠汇,使那辆大巴车化作了一尊漆黑的、长出四个轮子的棺椁,那座棺椁,在刹那之间,冲破了苏午气韵聚集而成的墙壁,碾向苏铨与郑春芳!:()我的诡异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