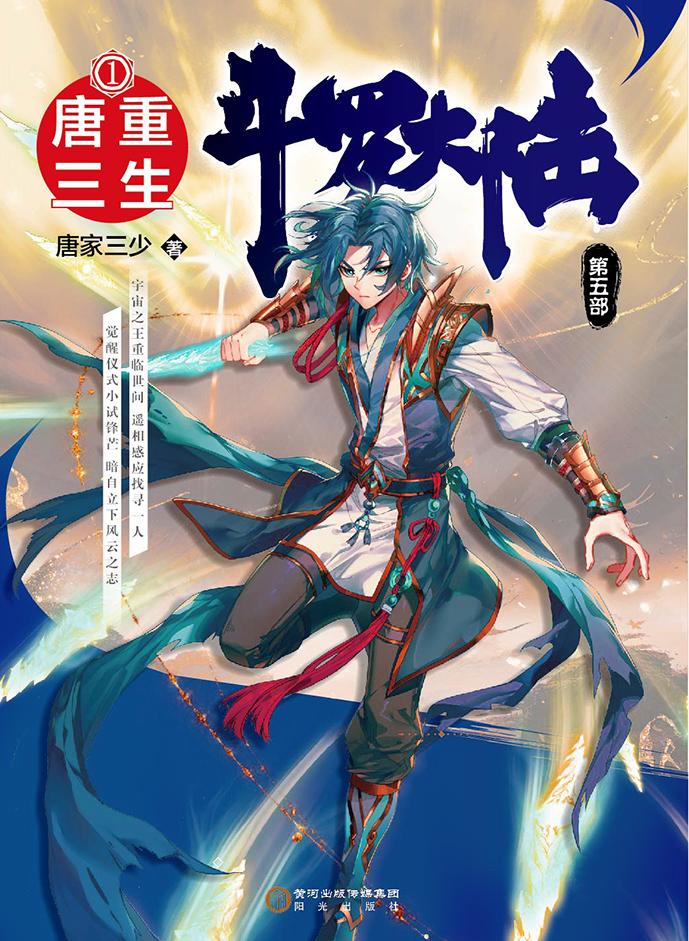秃鹫小说>流放后我在敦煌当汉商格格党 > 第74章(第3页)
第74章(第3页)
武卒心里一咯噔,他停住脚,跟小厮说:“我自己过去,劳你去找我爹来救我。”
说罢,他掏出身上零零碎碎的铜子和碎银子塞给小厮,催促说:“跑快点。”
武卒又急又怕,他清楚校尉的脾气,不敢在路上耽误,他一路快跑,进校尉府时他心里庆幸事情没闹到官府去,否则他不死也要丢半条命。
一进正堂,一个茶盏迎面砸来,校尉大喝一声:“混账东西。”
茶盏砸在胸膛上又滚落在地,摔成一地碎瓷,武卒慌忙跪地,他越过碎瓷爬过去,伏身认错:“卑职知错。”
见他一句反驳都没有,曲校尉就明白赵西平没冤枉人,他大步走过去,一脚把人踹个仰倒,“罔顾军纪,虚报生死,谁给你的胆子?”
武卒心里生寒,罔顾军纪这句话太重了,严重得能要他的命。他跪地求饶,说:“是赵母托我……”
一句话没说完,曲校尉又给他一脚,“真他娘蠢得让我心惊,你是赵家的狗还是我的兵?军纪在你眼里就是个虚设?”
“不敢。”
“不敢?”曲校尉嗤了一声,他冲外喊:“来人,把何青拉去演武场,请军棍。”
门外的守卫进来拖着武卒出门,曲校尉整理了下衣摆和头冠,他跟赵西平说:“这事传出去是我没脸,私下我让人打他军棍,这事就罢了,本官承你一个人情。”
“家母也有错。”赵西平请罪。
曲校尉摆手,他不信何青那人会听一个无知老妇的话,无非是他自己也有这个意思罢了。
赵西平带着隋玉跟曲校尉去演武场,曲校尉一到,手持军棍的守卫就开始行刑,手腕粗的军棍落在人身上发出一声闷响。
五棍下去,武卒身上的衣裳洇出血迹,此时门廊外一个头戴布巾的斯文老者快步入内,进门跪伏在地:“求校尉留我儿一命。”
“若不是看在你这个老东西的面子上,本官早打死他了。”曲校尉甩手,说:“二十军棍,一棍都不能少。”
二十军棍下去,人不死也残了。
赵西平动了下,他张嘴欲说话。
又三棍落下,空气中的血腥气越发浓重,隋玉看他这副惨状,心里的气没了。她出声说:“既然事关我二人,不如让赵西平代为行杖。”
赵西平身上有伤,举起军棍都艰难,若是让他去打军棍,接下来的十二棍就是做个面子功夫。
曲校尉没说话,那就是默认了,隋玉推赵西平一下,叮嘱说:“你小心点,伤口别裂开了。”
毫无力道的军棍杂乱无章地举起又落下,十二棍了,赵西平累出一头汗。
“多谢小娘子。”何账房过来冲隋玉道谢,又对着赵西平俯身长躬,随后给曲校尉磕几个头,这才走过去扶起何青。
“说说,你的目的是什么?”曲校尉问。
武卒汗颜,他瞥隋玉一眼,难为情地说:“我以为赵兄弟是被迷住心窍了,为个女人不要命了,想着他媳妇指定是个算计他的狐媚子,我就想让赵兄弟看清她的真面目。”
何账房兜头甩他一巴掌。
“蠢货。”曲校尉嫌恶。
武卒不觉得自己蠢,他是重情义,见不得赵西平被一个罪奴出身的女人玩弄在股掌间,为了个女人出去拼命,那才是蠢。
隋文安生离意
隋玉跟赵西平前脚刚回去,何账房后脚就拖着半身血的何青带礼登门道歉,恰逢做晚饭的时辰,半条巷子的人都听到动静出来围观。
“他身上的伤是校尉大人打的?”有人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