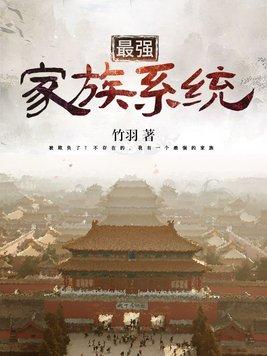秃鹫小说>花信风韩可彬 > 12chapter 12(第3页)
12chapter 12(第3页)
沈宗良掸了掸上头的枯屑,坐了上去。
他笑,拿出一支烟夹在指间,“难道我还会骗你不成?”
“哪里,小叔叔怎么会骗我们小孩子。”
且惠定了定神,大起胆子坐到他旁边,扭过头望进他的眼底。
沈宗良有一双优柔的眼睛,像倒映着雾霭的晨露,和他冷淡的面容相去甚远。
见他不说话,且惠匆忙撤回目光,晃了晃脚尖,“对不起,我刚才叫快了。”
“无妨。”沈宗良扬了扬手里的烟,说:“随你高兴。”
他语气很温和,眉间却压着隐约的疲倦和烦躁。
且惠又想起昨晚未竟的担心。她问:“你昨天很晚回来?”
“没回。”沈宗良的手搭在膝盖上,说:“写材料到三点,在办公室将就了一夜。”
她咦了一声,“材料不都是秘书写的吗?怎么还要你亲自动笔啊。”
沈宗良慢条斯理地说:“是份急件,上面催得很紧,与其秘书写完我再去改,不如自己写。白耽误时间不说,还多一个人辛苦。再者,不管谁来写,都不是我那个意思。”
其实他只要说一句,我习惯了亲力亲为,就可以带过这个话题。
可他看着且惠,解释地非常详细,甚至用上了再者。
沈宗良本来话少,昨晚工作了一夜,还要来应酬雷家的球场开业,拢共没睡到四小时,实在是累极了。
但面对小姑娘稚气的问询,总是不忍心三两句打发她。
可见谈话这么琐碎的事,也是需要讲一点机缘的,很玄妙。
且惠说:“沈总这么地体恤下属,是一位好领导。”
沈宗良勾了下唇,声音寡淡,“这下你又知道了?”
霍霍的风从身后吹来,长马尾扫在且惠脸上,她手忙脚乱地去抓住,用力嗯了一下。
他手指动了动,忽然很想伸手帮一下她,但终究没有这么做。
沈宗良转头看向前方,问:“今天没去赚生活费?倒肯花时间来消遣。”
且惠双手撑着树干,她自嘲地说:“上午去过了。当完了小钟老师,也来当当钟小姐。”
风太大,她索性把皮筋扯下来,散开头发,信手编了个油松大辫。
他笑了笑,“敢情钟小姐就喜欢自己坐着?谁也不搭理。”
“这你可冤枉我了。本来谦明和我说话呢,你一来,他就立刻去应接你了。”
且惠偏过脖颈,往他那边看了眼,无奈地耸肩:“谁让你是沈总呢。”
她声音很软,摇着手中的绿榕叶,像某种娇嗔的指控。
沈宗良从善如流地点头,“嗯,那的确是我来得不好。”
且惠吸口气,拨了一下鬓边垂着的刘海儿。
她说笑完,有些落寞地低头,“没有,跟你开玩笑。其实是没人理我。”
不必她来说,方才沈宗良也看得够清楚了。
她像是这场聚会里的一样摆设,就只管美丽精致地坐在那里,不派任何社交用场。
而钟且惠呢,尽管无人问津地独处,脸上仍然恬淡自得,唇角甚至抿着一弯笑。
那副清微淡远的模样,仿佛是在说,你们自去交际你们的,她犯不着凑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