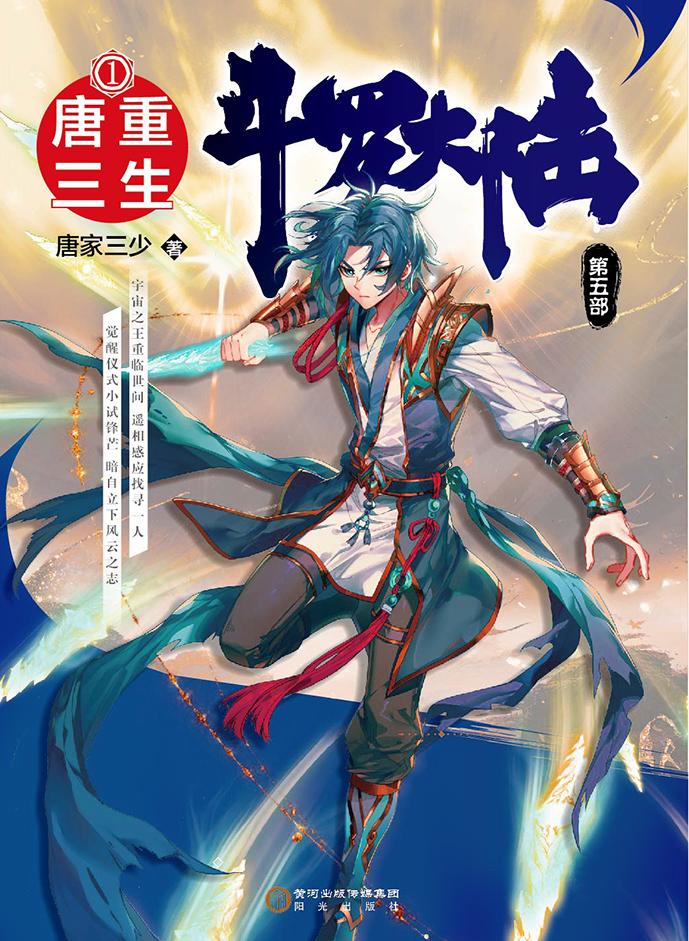秃鹫小说>五魁电影免费观看 > 第2章(第2页)
第2章(第2页)
现在,他们挡住了去路,或许是心情不好时听到欢乐的唢呐而觉愤怒,或许是看见了接亲的队伍抬背了花花绿绿的丰富嫁妆而生出贪婪,他们决定要逞威风了。
接亲的队列自是乱了,但仍强装叫喊:“大天白日抢劫吗?这可是鸡公寨柳家的!”
拦道者带头的听了,脸上露出笑容来,几乎是很潇洒地坐下来,脱下鞋倒其中的垫脚沙石。
以手做小动作向接亲人招呼,食指一勾一勾地说:“过来,过来呀,让我听听柳家的源头有多大哩?”
接亲的人没敢过去,却还在说:“鸡公寨的八条沟都是柳家的,族长的小舅子在州城有官做的,今日柳家少爷成亲,大爷们是不是也去坐坐席面啊!”
那人说:“柳家是富豪之家我们是知道的,但也没功夫去坐席,可想借这一点嫁妆柳家是不稀罕的吧?”
后生们彻底是慌了,他们拿眼睛睃视四周,峁梁之外,坡陡岩仄,下意识地摸摸脑袋,将背负的箱、柜、被褥、枕头都放下来,准备作鸟兽散了。
柳家的陪娘却是勇敢的女流,立即抓掉了头上的野花,一把土抹脏了脸,走过去跪下了:“大爷,这枚手镯全是赤金,送给大爷,请大爷您抬开腿放我们过去吧!”
陪娘伸出戴有多半尺长镣铐的右手,右手腕子有闪光的金色。
按理来说,一个下人,一个克死过三个男人的丧门星,是既不配戴钢铁的手脚镣,也不配戴足金的手镯的。
但谁叫她是柳家的下人,还是柳老太太的体己人呢?
近水楼台先得月,便是这个道理了。
前朝时允许有世代卖身的家生子存在,若是奴大欺主,或受不住主家的苛待逃了,主家告于官家,会发海捕文书通缉的。
而本朝说甚么共和了,竟没了皇帝,又不允许蓄养奴仆,柳家的家生子便散了一大半。
尊贵的柳家太太总不能亲手干活吧?
她守寡了20年,吃斋念佛心善,便收拢了一些像王嫂这样的无儿无女的无处可去的寡妇当下人,其中王嫂又是最得用的,日子过得比寻常中农还要好,甚至都戴上了金镯子。
土匪带头的走过来欲卸下手镯,但一扭头,正是藏在五魁背后的新娘从不太大的盖头中探出头来瞧情形,四目对视,新娘自然是低眼缩伏在了五魁的背后,那人突地笑了。
陪娘央求道:“大爷,这可是一两重的真货,嫁妆并不值钱的,只求图个吉祥。”
那人说:“可惜了,可惜了!”
陪娘说:“只要大爷放过我们,这点小意思,权当让大爷们喝杯水酒了!”
那人说:“这么好的雌儿倒让柳家消用,有钱就一定要有好女人吗?你家少爷能,我们白风寨也是能的。”遂扭转头去对散坐的同伙说,“睢见那雌儿了吗?好个可人儿,与其让她做财主婆真不如截回去让大伙玩玩哩!”
同伙在这一时里都兴奋得跳起来。
陪娘银牙一咬,突地一股赤胆忠心充塞胸口,看过的忠仆护主的戏文、听过的知恩图报的故事、受过的柳家太太的千般好处像流水般掠过心头。
她“砰”地一个头磕在地上,大声央求道:“大爷!大爷!您行行好!饶过我家少奶奶吧!我愿意替少奶奶服侍大爷们,做牛做马,绝不后悔!”
打头的玩味地笑了:一个不算年轻的下女,就算她是戴钢铁镣铐和金镯子的体面人,又怎比得上即将做财主婆的雏子?
但看在她的勇气份上,也不妨陪她戏谑一番。
于是他既不答应,也不拒绝,只笑道:“这样吧,先让我们看看你的决心。你将镣开了,脸擦干净,按照新娘子的模样将自己绑好,如果这都做不到,刚才说的自然是不得数的。”
自我牺牲的感动已经充塞了王嫂的全身,她一个嫁过三个男人又克死了三任丈夫的丧门星,死了都不知道跟哪个男人在地府相会哩。
能用这么一具残败之身换少奶奶跟少爷的和和美美,还有什么不知足?
柳家太太天天在念叨:雁过留声、人死留名。
她王李氏今天便要以忠仆护主的故事,在这黄土原上留名啦!
或许死了后还能在地府中得个好优待哩,也就不用天天担心下去后该跟那个男人相会的问题了。
于是她咬紧牙关跪直了身子,从水囊中倒出水来洗干净脸,取出钥匙开了自己的手脚镣,再脱下鞋袜放在一边,露出一双大脚来。
这双脚的底板既有着些劳动人民的茧子,又因为几年的清闲而白嫩了很多。
在众人的眼光中,陪娘不安地由跪姿转换成坐姿,局促地蜷缩起脚趾。但很快就豁了出去,从小包中取出绳索要将自己的膝盖绑紧。
带头的土匪咳嗽了一声:“衣裳太厚了吧?新嫁娘可不是这样的。”
陪娘全身一震,几乎要哭出声来,她含着两包泪水望着对方,小心翼翼地哀求到:“大爷…求求您…”
要知道,新娘上绳是需要全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