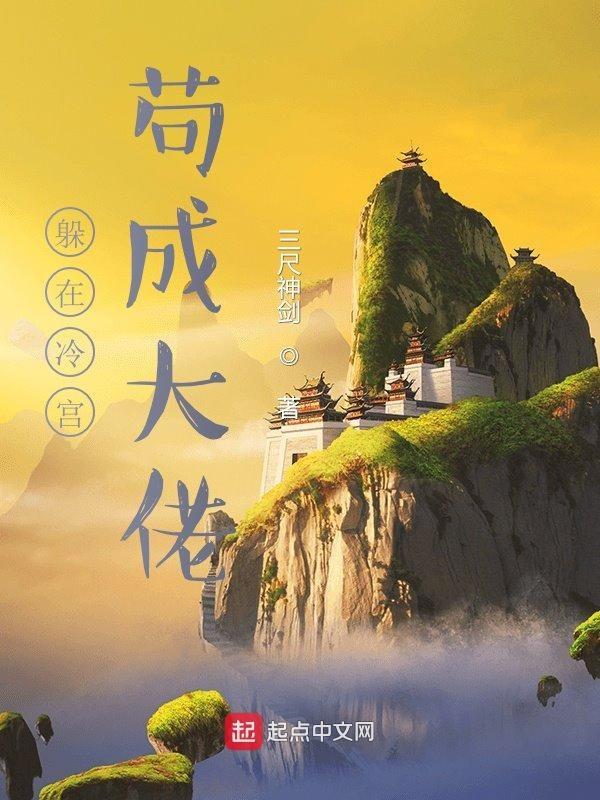秃鹫小说>飞机杯变成妈妈了还能用吗 > 第37章 人妻感的妈妈(第10页)
第37章 人妻感的妈妈(第10页)
洗菜池里漂浮着冰碴子,我拧开水龙头时被冷水激得一颤。母亲突然伸手过来,柔嫩的指腹擦过我手背。
“用温水。”她旋开另一侧龙头,蒸腾的热气立刻模糊了视线。厨房里响起她剁排骨的咚咚声与我撕豆角的脆响,此起彼伏。
砂锅开始咕嘟咕嘟冒泡,党参鸡汤的醇香混着当归的药香在室内流淌。
母亲揭开锅盖的瞬间,白雾攀上她的睫毛凝成细碎水珠。
“尝尝咸淡。”她舀起一勺金汤吹了吹,手腕一转却把汤匙递向我。
这样的场景重复过千百次,可当她温热的呼吸拂过我耳际时,我仍会想起儿时发烧那晚,她也是这样给我喂药。
油烟机轰鸣声里,青椒下锅爆出滋啦脆响。
母亲颠勺的动作行云流水,绛紫色围裙带子在腰后晃成蝴蝶。
我偷偷把冻得通红的指尖贴上她后颈,她惊得差点把锅铲甩出去,转身作势要拧我耳朵,眼底却漾着笑纹。
炒肉片的酱香混着白灼菜心的清香,在暖气房里酿成令人安心的味道。
当我们终于把六菜一汤摆上餐桌时,糖醋排骨的琥珀色浆汁正顺着青花瓷盘蜿蜒流淌。
母亲摘围裙时勾散了发绳,黑色长发瀑布般泻在肩头。
她舀了满满一碗虫草花鸡汤推到我面前,汤面上浮着的枸杞像朱砂痣。
“慢点吃。”她嘴上这么说,自己却把酸辣土豆丝拌进米饭里吃得两腮鼓鼓。
我夹起颤巍巍的虎皮蛋往她碗里塞,蛋黄流淌的瞬间,她鼻尖沾了星点油光。
窗外雪下得更密了,而屋内清蒸鲈鱼的鲜气正攀着窗帘往上爬,在吊灯周围织成暖黄色的网。
餐碟将空时,母亲变戏法似的从烤箱端出糖油粑粑。
焦糖色的糯米团子盛在荷叶边瓷碟里,咬开时黑芝麻馅烫得我直吸气。
她笑着用纸巾接住我嘴角漏出的糖浆,无名指上的金戒指闪过微光——那是上一年我们逛街时,我拿竞赛奖金买的生日礼物。
午餐后,妈妈躺在沙发上看电视,而我则是在厨房里洗碗。
洗碗池的水声哗哗作响,我将最后一个碗擦干放进橱柜。
客厅里传来电视剧的声音,偶尔伴随着妈妈的轻笑声。
冬日的午后总是格外静谧,连空气都显得懒洋洋的。
收拾完厨房,我走到客厅。妈妈正躺在沙发上,毯子松松地搭在腰间,长发散落在枕头上。她看着电视里的综艺节目,时不时发出一两声轻笑。
我蹲在沙发旁,轻轻替她把散落的头发挽到耳后。妈妈侧过头看我,眼睛里还带着午饭后的困倦。
累了?我问。
嗯。她伸了个懒腰,年纪大了,中午就不该吃饭,应该午睡才对。
我笑着摇摇头:妈,你还不到四十呢。
在你面前,总觉得老了。妈妈的声音轻柔,带着撒娇的意味。
我俯身在她额头上轻轻一吻:傻瓜,怎么会。
妈妈顺势倒在我怀里,她的体温透过家居服传来,暖暖的。电视里的声音渐渐变得遥远,此刻世界上只剩下我们两个人的呼吸声。
下午想做什么?我问道。
随你啊。妈妈的声音里带着倦意,反正都放假了。
我把遥控器拿过来,调低了音量。新闻频道正在播报天气,说是下周会有一股冷空气南下,气温又要下降了。
那今天下午我们就窝在家里好了。我轻声说,看电影,喝下午茶,什么都不用想。
好啊。妈妈的声音已经带上了一点睡意,不过茶就不要了,咖啡倒是还可以来一杯。
我扶着她躺好,又给她盖了层毯子。妈妈在我膝上蹭了蹭,找了个舒服的位置。她的呼吸渐渐变得绵长,像是在我的怀里找到了最温暖的地方。
睡吧。我轻声说,我在这儿守着你。
妈妈的眼皮子已经开始打架,但还是固执地不肯闭上。小伟…她突然开口。
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