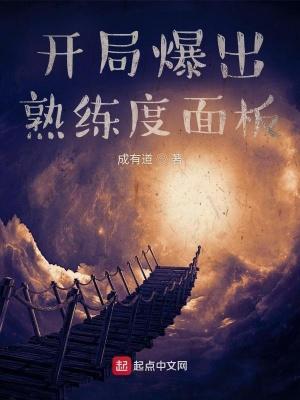秃鹫小说>凤鸣朝阳的拼音 > 110120(第16页)
110120(第16页)
大玄可不止他一位藩王。
倘若四方藩王接信后,果然都带兵入京,那谢氏还能全身而退吗?陈稚应略感烦躁地搓了搓指腹。
他是近水楼台,如果他先做这个勤王功臣,助陛下渡过此难,和亲的事不但能免,他在宗室的地位也将进一步水涨船高。
可陈稚应也没忘,谢家和宫里之所以闹到今天这个地步,起因正是谢澜安为了保他的女儿不远嫁和亲,而与陛下据理力争所致。
他真在此时背后捅刀子,道义不道义的且两说,闺女的眼泪就能把他淹了。
陈稚应的胡髭随着他咂唇的动作轻动,眼底光亮闪烁不定。
出入天子之家,又活到他这把岁数,早已不是讲究兄友弟恭,或仅凭一腔意气做事情的愣头青了。陈稚应大小是个藩王,他密切关注京城风波的这半个月里,内心深处,不止一次冒出过一个阴暗的念头:倘若,放任谢家人先除去皇帝,那么他是否有机会够一够那把椅子?
天下至尊谁不想当!但麻烦的是,陈稚应现下判断不出,谢逸夏究竟想扶持幼主上位,还是有自立之心?
如若是前者,那么有名正言顺的继承人在,就轮不到他这个堂叔。
如果是后者,谢氏都放弃保陈氏江山了,又岂会甘心托举他上位?
愁啊!陈稚应拍着自己的脑袋瓜,这运筹帷幄的事儿,他是真不灵光。
眼前闪过谢二那双一笑起来狡似狐狸的凤眼,陈稚应又打起了退堂鼓。论谋略,他算不过,论带兵,他也未必打得过,论儿辈才品,他膝下那几个成日斗鸡玩物的臭小子,不说比谢澜安了,就是加在一起能有谢家大郎一半出息吗?
倒也不止他家金玉其外,会稽王又给自个儿往回找补,放眼几个藩王后辈儿孙,又有谁能比肩谢澜安的治世之才?
谢逸夏得她辅佐,真是得天独厚。
这一想便想得远了,等陈稚应回过神来,余光里映入一角月色裳裾。
却是陈卿容睡不着,见前堂还有灯光,便披衣走了进来。
“囡囡哟,”陈稚应一见女儿,紧锁的眉心马上松开,下意识盖住手边的密旨,“还下着雨呢,这个时辰怎么还不休息?”
陈卿容噘起了嘴,含着小女孩般的抱怨:“蓉蓉生产后据说一直养不好,女儿几次想进宫陪陪她,爹爹你都拦我,哪里睡得着嘛!”
傻闺女。陈稚应在这非常之时哪里放心让女儿进宫,到时再被陛下扣住,他上哪哭去?
“爹爹……”陈卿容见父王面色不豫,不似平常模样,上前两步,“您怎么了?出什么事了吗?”
陈稚应沉默须臾,对女儿笑了笑。
“无事,天大的事也有父王呢。你快些去睡,叫人给你撑好伞,自己提着灯仔细看脚下。”
陈卿容有些不情不愿,但还是被父亲劝回了。离开前她掩唇打着哈欠说:“那父王也早歇,不许熬夜。”
陈稚应站在光影交界的门槛,凝望女儿的背影。
良久,他似下了某种决定,唤来自己的副将:“刘呈。”
“将出府的每一扇门洞开,多分派些人手巡值,守好夜。”
刘副将愣了下,以为自己听岔了,“王爷的意思是,将府里通往外街的前后大门都……都打开?”这大半夜的?
“不止前后大门,还有杂役走的门、角门、甚至狗洞,”陈稚应说,“全打开。”
郡主变公主,王公作皇帝,是很风光,可那需要他以命去搏……陈稚应自问,做不到谢家叔侄那么疯。
·
“女郎,会稽王仍未调兵。”允霜脚底生风地进了厅子,对谢澜安禀报,“但是王府的外门忽然明晃晃地大开,没有人出。”
夜半开门?玄白诧异琢磨,这是什么意思?
“这是给我们看的意思。”谢澜安唇角轻动,瞥着胤奚送她的明光扇上蝉薄锦面的纹路。
“会稽王是想让我放心,他不会有任何动作传递。他两不相帮。”
陈稚应有自己的考量,如果这一局过后皇室翻盘,他大可以说没收到过密旨,他扣押送信之人,为的就是留个后手。而若谢氏赢了一筹,那他今日袖手之举,已经是个天大的人情。
皇帝是陈稚应的亲侄,他不助天子已是极限,不可能带兵帮助谢氏。毕竟他还姓陈。
“这便足矣。”谢澜安反扣折扇。两刻钟前,她已令人强将荀尤敬送回府邸。她忽略老师怅痛复杂的眼神,只是冷静地分出一队人马,到荀府保护老师同师母的安全。
她不能再有被人拿捏的软肋。
“含灵,你想做什么,动作要快了。”
更漏滴答不绝,谢逸夏手里的清茶换成了酽茶,从旁提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