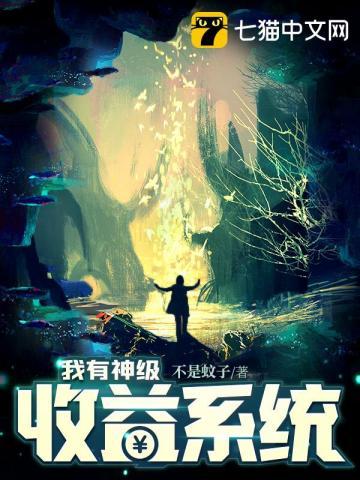秃鹫小说>和离后攻了心机帝王番外 > 100108(第26页)
100108(第26页)
萧挽呼吸一窒,反应过来后连忙去看舒白,眼下天才蒙蒙亮,室内光线昏暗,舒白的面容隐在暗处,萧挽看不?真切,只?能依稀看见舒白抿成?直线的唇。
萧挽扭过头?问游左,“来人是谁?”
游左嘴唇轻颤,“一共两辆马车,马车里的人没有露面,但这次随行的侍卫皆穿飞鱼服,我想?……里面的人来头?不?会太小?。”
话说到这里,马车里的人是谁已经?不?言而喻。
萧挽抿唇,对舒白道:“使臣的事情一直由我交接,这次是我疏忽,抱歉,我愿意?领罚。”
“不?怪你。”舒白捏紧手中信纸,指节泛起青白,语气?还算平静,“对方?上次就是有备而来,是我自?负大?意?,疏于?管教,料到虞策之耐心?将尽,以为还能再拖他几日,却没想?到他身为皇帝,竟然敢这样乱来,我的话他当真是一句都不?听。”
“如果真是那位,我们不?得不?谨慎对待,眼下南境和大?梁关系尴尬,一旦千金之躯受损,后果不?堪设想?。”陆逢年说,“趁着江齐峦他们没发现前,立即让他撤走是最稳妥的。”
“他既然来了,又怎么肯轻易离开。”舒白站起身,拢着身上鹤氅走了两步,语气?冷沉。
虞策之的到来无疑在计划之外,但既然来了,她也有把握护他性命无虞……
舒白拍了拍陆逢年的肩膀,道:“一切照计划进行,帝王亲至,对我们而言未必不?是一种保障,我会和他在一起,时时看顾,你们不?必分神。”
“你的身体……”萧挽担忧。
“修养多日,我的身体恢复差不?多了。”舒白轻描淡写,“别担心?,休息了这么久,也该活动活动了。”
以防万一,死士伪装的侍从将不?请自?来的大?梁使者请到了太守府内围的某个宽敞屋子,屋子逾制建造,是七进八出的二层楼阁,四?面有门,门外环绕游廊,游廊外则是江齐峦倾尽南境之力,用金银玉石堆砌的阆苑蓬莱。
舒白在去往屋子的路上,从死士嘴里得知了大?梁来使的名单,毫无悬念的,虞策之赫然在其?列。
好在虞策之也不?是莽撞无脑,相反,疯癫的行为过后,每一步都是精打细算的谨慎和算计。
此次进城,虞策之不?仅卡着南境能容忍的最大?限度带来随行近卫,还以那两辆驶入南境城内的宝马香车为遮掩,每一辆马车中都藏满了以一当十的暗卫。
小?皇帝显然豁出去了,舒白一想?到虞策之是坐着人挤人的马车混入的城池,眼中便不?由自?主浮现笑意?。
不?过话说回来,人心?都有阴暗面,舒白起初会不?受控制地怀疑,虞策之卡在这个时候来,有没有可能是想?和江齐峦里应外合。
毕竟在她和江齐峦的博弈中,一旦江齐峦胜出,她眼下拥有的一切都可能退回原点,大?梁的军队就驻扎在南境城三十里外,只?要虞策之在事后及时控制住江齐峦,南境十八城尽在大?梁囊中。一箭双雕,正中虞策之下怀。
但很?快舒白就否决了这个想?法,不?是因为笃定虞策之不?敢,而是因为实?施上难度太大?,连她这个幕后操守,都不?能摸准江齐峦部将的劫狱时间,虞策之远在大?梁军营,又如何能掐准时间,箭在弦上的时候打她一个措手不?及。
将不?可能的因素排除,最后剩下的就是昭然若揭的答案。
虞策之带了这么多护卫死士,宋祁崔溟亦跟在身边,他来势汹汹,显然不?是为了自?保,而是掳人。
舒白几次三番的拖延早就引起虞策之的警觉,加上虞策之本就是瞒着满朝文武,私自?随军同行,纵然朝中有几个心?腹老臣顶着,算上往返路程,眼看两个月转瞬即逝,回朝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情。
回朝在即,又察觉到她久留南境的打算,虞策之不?急才怪,他在最大?限度内召集精锐,已然动了软的不?行来硬的的念头?。
虽然在此时将小?皇帝形容成?狗有点煞风景,但虞策之的行为怎么看怎么像狗急跳墙。
舒白站在虚掩着的门扉前,拢着鹤氅,眉宇微沉。
“主子,外面冷,为何不?进去。”游十五低声提醒。
“不?急。”舒白平静地说,“你去替我办件事,附耳过来。”
阁楼曾是江齐峦某个宠妾居住的屋宅,不?同于?会客的厅房,这里的保暖做得极好,只?要关紧门窗,地龙烧起来,比春日还要温暖几分。
大?门‘吱呀’一声打开。
负手立在屋子中央的年轻皇帝顿时转身,灼灼的目光落在舒白身上,眼神赤忱执着。
虞策之三步并作两步,快步走到舒白面前,仗着广袖宽袍,毫无顾忌地和舒白冰凉的手十指相扣,
“夫人。”他的语气?温和,往日锐利的眉眼此刻微微耷拉着,看上去乖巧极了。
舒白熟知虞策之心?性,见他装成?乖巧顺从的模样,更加笃定了自?己?的猜测。
若是平常相处,虞策之变着法子和她作对,惹她生怒,生怕激不?起她负面的情绪,眼下卖乖弄俏,不?过是自?觉心?虚,为真正能令她愠怒的事情做铺垫。
舒白没有立即发作,目光平静地望着他得天独厚的面容:“阿拾,你很?不?听话。”
虞策之攥着她的手一紧,表情有些僵硬,但很?快恢复如常。
他垂下眼帘,语气?温吞和缓,“抱歉,我很?担心?你。”
“担心?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