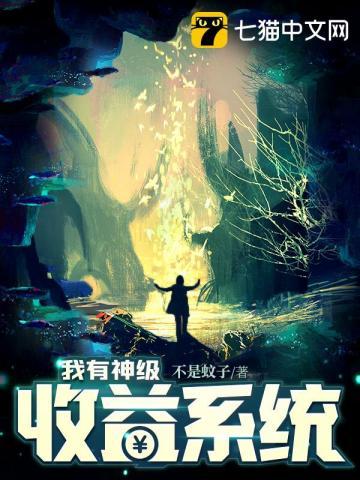秃鹫小说>和离后攻了心机帝王番外 > 100108(第25页)
100108(第25页)
月色西沉,眼看即将到众人约定起事的时辰,闻缺扭头?问霍耀风,“我再问你一次,你确定这个点牢狱的守力是最薄弱的吗?”
霍耀风神色坚毅冰冷,冲闻缺点了点头?,“确定,我在这里蹲守很?多天了,这个点守卫最喜欢打盹,且近来舒白的身体怕是出了什么乱子,调了城里大?半的兵力回太守府守着,今日闻将军带来的府兵皆是精锐,区区几个偷懒的衙役,我们完全能应对。”
霍耀风仔细打量闻缺神态,见只?差临门一脚,闻缺竟然有打退堂鼓的意?思,连忙又道:“我父亲曾任户部尚书,来南境前我们就确认过,大?梁粮草不?足,如今频繁派使者来和谈,便是大?梁粮草将尽的证明。”
“但江太守失去太守印,沦为阶下囚,大?势已去,南境眼看已经?是那个丫头?片子当家,难以撼动,我等何必非做这种吃力不?讨好的事情。”
不?等闻缺话音落下,霍耀风倏地攥住他的手臂,冷然道:“闻将军驰骋沙场多年,难道真的愿意?被一个不?知道从哪里冒出来的女人骑一头?吗,再者,亲近卫羽一派的文臣守将皆受到舒白重用,你们被舒白骑在脑袋上便算,闻将军,你真的愿意?对迟陇之流毕恭毕敬吗。”
闻缺眯起眼睛,面部肌肉抽搐一下,显然被霍耀风的话激怒,望向霍耀风时,眼神不?善。
霍耀风心?跳得飞快,却知道这时候自?己?不?能露怯,他必须说服闻缺,这不?仅是借闻缺的手为父亲报仇,同时也是保住他自?己?的性命。
霍耀风压下心?中的酸涩,不?敢回想?一年前的自?己?是如何春风得意?,现在又是如何辗转求存。
他强装镇定道:“有件事,只?有我知道,我想?闻将军一定需要听一听。”
“什么?”闻缺看了眼不?远处松懈的守卫,不?耐地问。
“南境离京城甚远,将军和诸位守将就算已经?派探子去打探舒白的底细,一时之间也得不?到什么有用的消息,毕竟舒白背靠宫中那一位。”霍耀风缓缓说。
“宫中那一位?”闻缺猛地睁大?眼睛,反手抓住霍耀风的手臂,“你是说舒白是皇帝派来的?”
“不?止,若没有南境的叛乱,虞策之已经?力排众议,立舒白为后了。”霍耀风仔细观察闻缺表情,知道自?己?成?功笼络了闻缺,“救出江太守后,以江太守的名望,足以一呼百应,到时候我等将舒白关押起来,用她要挟大?梁,逼大?梁承认南境非大?梁州郡,而是与大?梁同等地位的国家。”
“最好再逼虞策之把玄荼城划给南境,大?梁粮草不?足,短时间南境不?会再受大?梁倾轧。”霍耀风说,“闻将军,到时候您不?仅是头?功,而且是南境的救命恩人,前路坦荡,不?比眼下的局势好吗?”
闻缺被霍耀风说动,逐渐狠下心?来,扭头?看向自?己?的副将,“动手。”
夜色如泼墨,身着黑衣训练有素的府兵蜂拥而上,只?是眨眼功夫,便解决了松懈打瞌睡的守卫。
得到闻缺允准,府兵抽出刀剑,搜出守卫身上的钥匙,快速进入牢狱。
一切都顺利得超乎想?象。
霍耀风没有进入牢狱,而是和闻缺几个守将在牢狱外的灌木后藏匿,霍耀风的心?脏始终高悬,砰砰跳个不?停。
面对闻缺时,他巧舌如簧胸有成?竹,但劫狱究竟有几分把握,连他自?己?也无法估量,他没得选,只?能赌一把。
时间一点点过去,不?知不?觉间,鸟鸣声都悄然止住,寂静无声。
霍耀风只?觉得他的呼吸都开始凝滞,他们等了太久,他明显能感觉到,闻缺和其?余几个守将已经?开始不?耐烦了。
就在霍耀风打算说点什么缓解气?氛的时候,紧闭的牢狱大?门倏地敞开,府兵陆续从牢狱中出来,片刻后,两个府兵将戴着枷锁脚镣,气?息奄奄的江齐峦搀出来。
霍耀风心?中的大?石倏然落地。
谢天谢地,天不?亡他。
成?了!
无论南境城内如何暗潮汹涌,第二天还是不?可避免地如约而至。
翌日清晨。
舒白一夜未眠,她裹着厚实?的衣物,头?发披散在身后,用一根红带松松垮垮束起,坐在案几前处理政务。
游十五在她身侧汇报昨晚各方?人员的一举一动。
陆逢年和萧挽则立在案几前,随时等候舒白的调遣。
舒白听完游十五的汇报,没有立时说什么,而是先提笔将递往大?梁的书信写好。
今日之后,一切都会尘埃落定,是时候给皇帝一个明确的答复。
舒白长眉轻蹙,虽然笃信虞策之已经?拿她无可奈何,但皇帝疯起来是什么脾性,会做出什么样的事情,便是她也无法预估。
这封送往大?梁的信件,她的措辞十分谨慎,在话里话外暗示久留南境之余,也明确写出,无论大?梁那边有任何异议,都可以继续派遣使者前来商定。
阅览这封由她亲笔所写的书信后,她知道虞策之一定会来。
到那时候尘埃落定,她打算同他好好谈一谈,心?平气?和的谈。
然而才将信纸装好,盖上太守印,游左急匆匆冲进来,面颊绯红,喘着气?道:“大?梁的使臣忽然来访,他们定是在之前哪次买通了城门看守,守卫竟敢私自?放他们进城,我们得到消息时晚了一步,现在他们已经?奔着太守府来了。”
陆逢年拧眉,冷声道:“江齐峦很?快就会攻入太守府,这个时候怎么能放他们入南境,出了事情谁也耽搁不?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