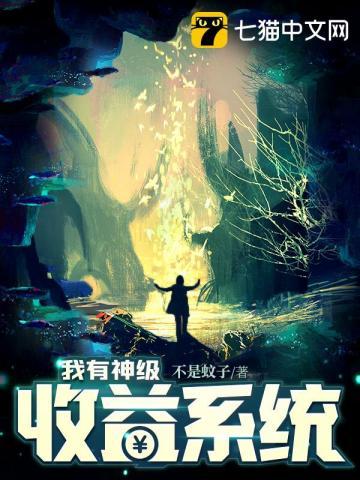秃鹫小说>眠春山讲的什么 > 第108章(第2页)
第108章(第2页)
徐祯一样样分拣好,还得腾出手拿了艾草搓的火绳子,四处点了熏蚊子。再拿上李郎中给的苦楝子喷虫药,沿着屋里屋外四处喷上一圈。
零零散散一大堆的事情,还好他手脚勤快也撑得住。
往常都是两人一起做,累一点的活徐祯担了,这时候起姜青禾真没空。
眼下有徐祯这个强有力的后勤,姜青禾则带着麦秆、芦苇杆和高粱秸、晒干的苞谷皮,提那一大篓的东西去找苗阿婆。
两人趁天还亮着去了染坊,这些草染上色得反复试验才成,至于为啥没叫宋大花和虎妮,明天她俩得天麻麻亮就下红花田摘红花。
摘红花太讲究,起了日头晒到的话,红花上的刺格外扎人。所以都是趁着天不亮,灰蒙蒙还有雾气时,红花隐隐有露水,就着湿哒哒的手感薅下来。
摘好的红花苗阿婆都得先细细挑拣好,再放到盆里用捣棍捶烂,装进毛口袋里到水渠边上一点点搓洗。
搓洗后端来发酵过一股烂酸味的粟饭浆,没伸手都能感受到湿滑黏腻的恶心感。可人手得放进去,将红花碎放在里头再反复淘洗,最后压出汁水,压到没一点汁才好。
这样出来的红花黏成一团,上手捏成饼,采了干青蒿盖上一宿,之后慢慢阴干后也不会发霉。
所以这几日苗阿婆都在忙这事,一进染坊,到处都弥漫着酸烂的味道。哪怕那些红花饼搁在单独的房间里,都掩盖不了这股臭味。
苗阿婆见姜青禾一副要呕的表情,笑了声,“待久了你就闻不到了,先煮料,俺先试试。”
她往灶里添柴时说:“人出去走走多好,得在镇上待一待的,苗苗你也别想太多,能赚咱就赚,染坊的事也别操心。”
苗阿婆的语气很温柔,“你只管去做你该做的,染这些草婶都给你包办了,羊毛染了,拿去叫大伙给搓着哩。”
“土长也叫人收了各家的麦秆,全都凑在一堆了,眼下还不是割芦苇的好时候,高粱不能收,可各家拿出了上年晒干的高粱叶,没要钱,只说用着呗。”
苗阿婆起身往锅里倒着染料,将她没在的时候大伙做了啥一一跟她说了。比如大热天汉子下完地,又一起进山去割灯芯草。这种草茎细又天然绿油油,编出来的扇子也别有风致。
有的就领着孩子去河滩边上,又或是柳树丛生的地界,折适合编织的柳条,有空就去折一堆捆好。
妇人齐心协力将这些柳条和灯芯草晾晒出去,这种细柳条得浸泡后,将皮剥开,实在没办法剥的,拿一把小刀在木板上反复刮皮,一点点刨,费时又费力。
而且这活计是她们自愿做的,只有搓羊毛线才是有钱拿的,可她们照样干得乐呵呵。
眼下社学没有学生了,改成把式学堂后,早先大伙很抵触来这里,可一趟趟往这走后,他们也都习惯有个地方坐着闲拉呱。
而且他们见社学破破烂烂的,哪哪都不咋样。有些人家拿了盖屋还有剩的瓦出来,几个汉子搭了梯上去盖瓦,将碎掉的瓦片给扔掉,一层层叠好。
也有拉着牛车,几个哄伴去挖土,顶着热天烧了两天的窑,烧出一堆砖块,把篱笆院墙给拆了,又新砌了一圈。
然后给院子大半铺了砖,其余的平整土地,尤其后院给倒了土,叫周先生可以种菜。
还换了门和窗,如今真是大变样了,桌子也请了徐祯做成好几张圆桌,大伙可以围着说话,站台加高,更叫人看得清楚。
所以如今晚上闲暇,妇人都会来这里,拿了羊毛线,又或是柳条还是灯芯草或麦秆,要么用拨吊转羊毛线,要么是拿了柳条开始编。
正是这地让大伙都聚在一起,编东西时也能相互多瞅一眼,你学学我咋编的,我再从你这上头改一改。
等有些编筐一出来,摆在一起,自然发现花色比前头竟要好看不少。
有转羊毛线的妇人瞅着那小巧细密的编筐说:“要是搁市集上看到,俺能多瞅几眼,说不定真的会买哩。”
“这色你都想买了,染了色编的那你不得上手抢,”枣花婶笑话她。
可她的话让大伙都陷入了幻想,草真染了红,那编出来得多好看。
她们一时无比期待染坊能染出色来。
可这头进行得不算顺利,玉米皮和高粱皮毫无疑问是最好上色的,可眼下压根没到采收的时候。
芦苇杆厚重皮光滑,染色并不好染,哪怕反复在染料里浸煮,都很难吸色,染出稍微艳一点的红。
至于麦秆,浸水后上锅反复煮,倒是能染色。但颜色不好,得多次染,明矾上去固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