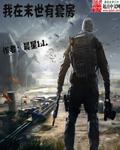秃鹫小说>摆烂这个词是从哪里传出来的 > 3040(第8页)
3040(第8页)
徐碧荷道:“只是揣测元帅意图,就算咱们意会错了,元帅宅心仁厚,不会计较的。”
唐折桂意动,被徐碧荷说服。
说不定正如徐碧荷说的那样,一切都在元帅掌控中,可能信还没送到元帅手里,丰城就出现意外状况,她不得不留在这里处理异常。
信送出去,唐折桂不着急离开,跟徐碧荷和吕飞燕一起修路,俘虏是她送来的,熟悉人,有看管经验,于是唐折桂负责盯着俘虏。
吕飞燕怕她不熟悉情况,带唐折桂在丰城里转了转,又去采石的地方亲眼看过,事无巨细地交代一遍。
“元帅性格仁善,咱们作为她麾下的部将士卒,一言一行都关乎外人对元帅的评判,不能肆意妄为,丢了元帅的脸,拖累整个忠义军。”
吕飞燕在徐碧荷和宋延芳的帮助下迅速上手,知晓诸多人情往来相关,以及处理文书、舆情的暗藏规则。
所谓见微知著,细节决定成败,百姓可以从日常小事里感知忠义军整体形象,越是微小的地方,越是要小心。
“虽说是俘虏,但也不能过多苛待,正常相处。”吕飞燕细声道:“对诚心投降的人,我们要接纳他,多一个人,多一份力,积小成大,相信我们忠义军会在怀宁、延临和丰城占据一席之地,以后亦将在晋州甚至整个天下占据一席之地!”
唐折桂听得热血澎湃,感叹接人待物里竟然还有这么深的门道,降服敌人不止打打杀杀一条路,还可以兵不血刃,不战而胜。
她转念一想,投降的敌军可以转化成自己人,为己所用,人越多,那她们的胜算岂不是越大?
唐折桂打起俘虏的主意,看向他们的目光愈发炽热,但她瞧不上手下败将,让她上赶着嘘寒问暖可一点做不到。
她只能憋在心里,别扭地盯紧俘虏,没折辱、欺负他们已是仁至义尽。
校尉忐忑,被唐折桂盯得发毛,她板着脸,像尊杀神,总感觉唐折桂早看破他想要逃跑的企图,故意跟在他身后。
唐折桂如幽灵四处飘动,校尉如芒在背,寻不到出逃时机,被迫歇下心思,在采石毕、吃饭路上悠悠想道:“此处饭食管够,没有挨打受气,不必日夜殚精竭虑,待在这里好像也不错。”
校尉待了一两日,很快便感受到这里的特别。
首先,一日竟有三餐饭食,午间加饭,这事放在贵人身上不足为奇,但放在普通百姓、士卒甚至俘虏身上就稀奇了,尤其当下每日能吃到一顿饭算是不错的态势,徐茂何其慷慨。
其次,士卒日常训练的场面颇为怪异,又是站定不动比耐性,又是排列队伍跑来跑去,还有比拼谁先一步爬树登高的,让人摸不着头脑。
校尉看不明白,在观察的同时尽力降低自己的存在感,默默寻找逃离之机。
而唐折桂的请求信送到徐茂手里,徐茂展开一看,喜上眉梢,巴不得她待在丰城里别出来,免得冷不防给她惊喜。
徐茂摸下巴思虑半晌,提笔回信:“外伤易见,内伤难寻,既然身体不适,你且寻个名望高的大夫看诊,摸脉瞧一瞧,在丰城安心养伤,不必着急回来。”
她怕唐折桂执意跑回来,另外吩咐徐碧荷和吕飞燕看紧唐折桂和同路折返的炊事班士卒,要求找大夫给她们一一摸脉象,检查内伤,务必健健康康地重回炊事岗位。
唐折桂她们这批作战凶猛的士卒退至丰城,自己身边应该再没有能征善战的人,阻碍倏地消失,即将迎接结局,登出游戏,徐茂松一口气,对晋州刺史的下次攻袭充满期待。
徐茂浑身轻松,进展不顺的晋州刺史可不好过,坐卧难安,他们一而再、再而三地攻袭失败,未能拿下徐茂,背负的压力越来越重。
外面的人不了解徐茂,只听她是女子便掉以轻心,不以为意,同他们最初的想法一样,好像随便派两个人即可解决怀宁变乱,殊不知真正对上此女,才知道杀她多棘手。
然而那些官吏不知内情,看上去仿佛是他们晋州的官员太无能,一直未能平乱,向他们投来轻蔑的目光,肯定少不了背后嗤笑,出动那样多兵马,抓不住一介女流。
仅随意想想,脑海里尽是一张张嘲讽的面孔,晋州刺史无比憋屈,焦虑地头发一把一把掉。
他跟在萧刺史身边干着急,如若被放架在火上烤,最后忍不住了,找萧刺史问道:“萧公,我们劫杀炊事、围困徐茂的计策不成,下一步应当如何是好?”
着急上火的不止晋州刺史一人,萧刺史的日子同样难过。
他如今肠子都悔青了,恨自己为什么要答应来晋州,接下这个烫手山芋。
他们连徐茂麾下烧火做饭的小娘子都打不过,可想而知跟随徐茂上阵的精锐之师那么强悍。
现在所有人指望着他,骑虎难下,萧刺史脊背浸出冷汗,表面镇定自若,实际急得团团转,嘴角燎泡。
萧刺史沉思良久,眼里闪过决绝,“既然围困一招不行,那只有正面应敌了,我们人多势众,一千人拿不下她,我不信一万人也杀不了她,绝不能放任忠义军壮大,成为朝廷难以铲除的祸患!”
“萧公所言在理。”
语毕,晋州刺史不由叹息,为今之计唯有以人数取胜,足以证明铲除徐茂的麻烦,祸患已成,哪需要他们特意戒备。
无可奈何,只能怪他一时失察,先前没有足够重视,给了徐茂攻占延临、丰城,发展人手的时间。
晋州刺史悔之晚矣,拱手应声,下去清点人马,做好背水一战的准备。
*
唐折桂接到徐茂的回信,捏着信封一角走来走去,心快跳出胸膛,浑身发烫,脑袋晕乎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