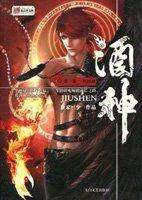秃鹫小说>爱者留痕在线阅读 > 第34章(第1页)
第34章(第1页)
辗转反侧的一整夜,像钝刀在切割神经。
报表上的数据难以入眼,梁倏亭用来勾画重点的钢笔悬空太久,当他终于决定要下笔时,笔尖已经干得无法顺畅书写。
他将文件合上,抬头看向窗外。
隔着一层玻璃,整座城市灰沉沉的,干燥、清冽。不降雨的冬日阴天就是这样,如同保管不当的褪色油画,不够鲜活,缺乏生机。
五分钟后,梁倏亭走出办公室,罕见地从公司早退。
梁母接到梁倏亭要回家的消息,提早从富太太的下午茶中退出,在家中等待儿子。她等来的是一个看起来毫无异常的梁倏亭,但她知道这只是“看起来”。梁倏亭在工作时间“翘班”回家看父母,这件事本身就极为反常。
梁倏亭靠坐在沙发上,梁母在他对面,能看清他眼里有淡淡的红血丝。他一定没有休息好。
“宁柠那边我都处理好了。”梁母给儿子倒了一杯热茶,慢条斯理地说,“他不会再来烦你和小戴,这一点妈妈可以跟你保证。”
梁倏亭接过热茶,说:“妈,谢谢你。”
梁母摇头:“不要谢我。这是我应该为你们做的。”
为了不再和宁柠有任何交集,梁倏亭选择让父母帮忙解决问题。实际上这也是正确的做法,因为不停地骚扰梁倏亭,还把收到的礼物寄给戴英,这类事情宁柠做得出来,却不一定想得出来。替他出谋划策的人是宁母,给他底气的人是宁父,那么让父母辈问题,才是彻底消除后患的唯一方法。
“可是小戴那边我就帮不上忙了。”梁母说着,和他开了个小玩笑,“总不会爸爸妈妈帮你把BOSS都都打掉了,你还不能通关吧?”
不妙的是,这个玩笑没能让母子俩笑出来。客厅里很安静,梁倏亭沉默了许久,才点点头,说“嗯”。
梁倏亭遇事很少逃避,又或者说,在他的观念里,“逃避”并不是一种解决问题的方案。但是当矛盾爆发,戴英说出“我宁愿你别来爱我”时,他的应对无异于逃避。
好像身处一场商业谈判,场面僵持不下,谈判双方的状态都达到极限,眼看着平衡就要崩塌,技术性的打断就必不可少。中场休息、吃一顿饭,甚至只是去趟卫生间、打个无关谈判的电话,都能松一松双方之间过于绷紧的那根弦。
“我们太激动了。”
“戴英,我们先各自冷静一段时间。”
“等我们都冷静下来,再重新讨论这件事。”
那天,梁倏亭的本能警告他必须中断谈话。于是,他用这样的话术掐断了他和戴英的交流。
风险太高了。
如果当时的对话继续进行下去,在各种可能出现的结果中,有一种是梁倏亭无论如何也接受不了的——在情绪的支配下,双方的言辞越来越尖锐,即使是冲动,即使事后会后悔,但是在那一刻,戴英说要分手。
光是想象,梁倏亭的太阳穴就疼得近乎裂开。
那天的对话,或者说争吵中断后,梁倏亭离开了戴英的出租屋,而戴英并没有和他一起回家。
第二天早上,梁倏亭在去见戴英的路上接到了他的电话。他告诉梁倏亭,他被公司派去了外地出差,归期不定。
梁倏亭将车急停在路边,听到戴英继续说,“我们下午就出发,你不用来送我。我在公司,晚点会和同事一起去机场。”
电话没有挂断,可是好长一段时间,双方都无话可说。
最后,梁倏亭说:“注意安全,落地给我打电话。”
戴英说:“好。”
就这样,他们迎来了一段堪称冷战的时期:见不到面,虽然还是会通电话,却一致地回避重点,例行聊完彼此的睡眠、天气和一日三餐,就挂断电话。
是梁倏亭先选择了避重就轻、粉饰太平。他退一步,就别怪戴英会退十步。他说要“各自冷静”,可是没有人能确定冷静的标准是什么,他们要过多久、变成什么状态才算是足够冷静。更糟糕的是,也许只有情绪激动的状态下,戴英才会把他掩藏的想法说出来。当他们恢复冷静,就再也无法触及到问题的核心。
梁倏亭为他们的关系规避了最坏的结果,换来的是一场轻微到恍若不存在,却顽固的、长久的“慢性病”。
“年会那天,戴英能来吗?”
母亲温柔的声音把梁倏亭从思绪的漩涡中叫了出来,她问,“你有没有好好地邀请他?”
岁末年初,大大小小的年会、晚宴和沙龙接连不断,梁倏亭收到了许多合作方和朋友的邀请,他主管的集团子公司也即将开办年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