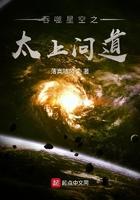秃鹫小说>一苇山河谣在哪里看啊 > 第29章 暗涌(第1页)
第29章 暗涌(第1页)
腥膻的白浆一注又一注地喷薄而出,浇在钵盂的壁上噗噗直响。
施礼压着那杆坚硬的肉棍对准钵盂,铜人浑身的肌肉都因高潮而剧烈滚动,那情动不自禁的脸上满是淫乱,原本肃穆持重的强者在欲念中表情失控,像个白痴,施礼心口亦砰砰直跳,这种控制强者的快感,既熟悉又陌生。
铜人大口喘着粗气,竟没想到自己泄得如此快,这小子虽然生涩,总强过罗汉堂的粗汉,起码光是看着那张樱红的小嘴含着自己的硕物就是一种享受,还想再泄一次,施礼却不肯了。
“师叔的奶我今日挤过了,再挤得明日了。”
铜人只好依他,细水长流,莫头一天就吓坏了这美貌师侄,明日又换糙汉来他可不肯了。
有了第一个铜人打样,施礼端着钵盂沿着洞窟石室陆续给其他十七头铜牛挤了奶,出得华严洞时,天都黑透了,他力乏疲惫,只有手中满当当沉甸甸的一钵浓精。
施礼一身狼藉,浑身上下都是雄性浓烈的腥膻,他用衣袖掩着钵盂的口,一路避着旁人,好容易回到罗汉堂复命,开门的法澄接过钵盂,顺手将那盆阳精浇入花池,吩咐他明日准时报道,便又关了院门。
施礼接过空空如也的钵盂,在门前愣了一会儿,突然觉得好生委屈,他肚子咕咕直叫,今日为了挤奶,除了几口躲避不及的男精,他什么也没吃,辛苦挤出的雄乳却又被人当面倒掉,原来挤奶是假,让他来做罗汉堂泄欲的工具才是真。
神尘坐在蒲团打坐,虽是例行晚课,却一直心系徒弟无法静心,直到院外传来急促的脚步,他连忙开门,却见施礼影子一晃而过,径直扎进了沁骨的溪水之中。
月光下那个影子瘦骨嶙峋,像一头惊慌无措的小鹿,神尘亦时常错乱,他的徒弟,真的是从前那个搅乱江湖的小太岁吗?
还是一切都是一场梦,过去的记忆只是一场错乱的玩笑。
施礼浑身抖如筛糠,哆嗦着在沁骨的溪水里盥洗衣服和身体,听身后异动,他以为是野兽,却见一道精壮的影子朝自己走来。
“师傅……”
神尘褪去一身衣袍,一丝不挂的酮体精实健美,完美得像一尊雕塑,施礼脸上一烫,别开头去。
“过来,师傅替你洗头。”
施礼仰躺在水中,头枕着神尘盘坐的大腿上,神尘把皂角在水里浸了浸,微微搓起泡沫涂抹在徒弟如瀑的黑发上。
“在罗汉堂可还习惯吗?”神尘的脸平静得像一潭深不见底的秋水。“不好,一点也不好。”
施礼本就委屈,听师傅问起,再忍不住,将今日所遇种种一五一十全与他说了。
慧业其人多么淫乱荒唐,神尘深有体会,但慧业如此安排,不会毫无缘由,断不会只是为了折辱施礼。
神尘剑眉微蹙,沉思问道:“你在华严洞中可还发现什么奇怪之处?”
“奇怪之处?”施礼蹙眉,给十八铜人挤奶还不算奇怪?
“对了,我给他们挤……嗯,挤奶的时候,他们都会固定摆出一种姿势,每个人都不一样。”
“何姿势?你还记得?”
施礼思索一番,随手捡起溪边枯枝画了出来。
神尘一看,当即会意,嘱咐道:“你每次去时,需得特别记住他们所摆出的姿势然后临摹下来。”
施礼当也不是傻子,那些姿势单看古怪,画出来便十分明了,已然一套练气的法门。
“师公这是想传功给我?”施礼颇有些兴奋,他一直想学武功,但他还是俗家弟子,是不能习武的。
神尘显然对他“师公”这个称呼不满,却也没有纠正他,只用木梳仔细地将他头发梳开。
施礼周身酸痛,手臂更是犹如千针在贯,给十八铜人挤奶简直比做一天苦工还累。
神尘又轻柔地替他按着小臂,叹道:“你若吃不消,我明日我再去一趟罗汉堂,你还是回地藏院做工吧。”
“不!我吃得消,只是第一天还不太习惯而已。”
可是……替人抚慰,实在不是一个光彩的活计,对于修身养性的僧人,这等淫秽之事,更是有损修行,他以为慧业会让施礼做些杂工,没想到……
施礼知道师傅心中所想,宽慰道:“既然师公是想偷偷传我功夫,这种活计也做不长,总好过在地藏院天天挨猪头欺负,庸庸碌碌也没个头。”
神尘不置可否,他现在的地位立场,实在保护不了施礼,可能还会连累其跟着自己受罪,罗汉堂是荒谬,却实在没有个更好的安排。
施礼痴痴地望着神尘刀锋般锐利的下颌线,师傅真俊,这天下怎会有这么好看的人。
神尘的胸腹微微起伏,紧凑地挤在一起,溪水映着月光漾起潋滟,投射在那麦色无暇的肌肉上,就好似无数双柔荑在抚弄师傅健壮的身子。
施礼再忍不住,猛地探头吻了一口师傅的腹肌。
“!!!”神尘一愣,周身都紧了。
徒弟的脸红扑扑,清澈的双眸中能瞧见自己的投影。
“今日给铜人师叔挤奶……他们还问我……”